时光深处的老街随笔
随笔,顾名思义:随笔一记,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是过去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随笔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由法国散文家蒙田所创的。以下是为大家带来的时光深处的老街随笔,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时光深处的老街随笔 篇1
周日我去了趟老家小镇,午后,独自徜徉在老街,一步又一步,踩着童年、青少年时代走过的路,仿佛走回了那久远的青葱岁月,见到老街勃勃生机的往昔。
老街,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1.5公里,中间隔着一条河,河上有座石桥连结着。
多年前,河水清澈绵长,河岸芳草萋萋。
老街两侧都是有些年头的老房子,有民居,有商铺,房屋多砖木结构,高低错落,参差不齐,春天,从两房交界的墙角边冷不丁探出可人的小花来。
路面,铺的是一排排不规则的青石板,石板大小不一,宽窄不等,材质粗细有异,因为常年的踩踏,高低不平,雨天,缝隙间常踩出一汪水来。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的家在离老街不远的地方。
那时,街道上有供销社、邮政局、新华书店、电影院、粮站、照相馆、刻字店、裁缝铺、小杂货店……年幼的我,最爱流连的是“老刘香货店”,店里的狮子头、麻花、烧饼、烘糕、米糖……常诱得我口舌生津,母亲给的零花钱,大多被我在这里修了“五脏庙”,为此,常被母亲骂为馋嘴猫。
读中学时,光顾较多的地方是新华书店,书店不大,存书量也不多,种类也较少。
除了一些中小学学习资料、儿童文学、印刷质量不太好的美术书籍和少量的民间故事及野史小说外,好像没什么书籍。
偶尔我也去“老李照相馆”,和几个死*集结拍照,臭美一番。
记忆中的老街,总是人来人往,人气兴旺,孩子们打打闹闹,年轻人说说笑笑,老人们闲聊散谈,主妇们家长里短。
到了集市日,老街更是一番繁荣景象,简直就是“清明上河*”再现。
日升三竿之时,人潮像水一样涌往街市。
集市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街道两旁除了沿街店门留个进出通道外,摊点一个挨着一个,摆满了大豆、花生、红薯、玉米等农作物和竹篮、铁锅、簸箕等小家什。
吃的用的,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叫卖声、吆喝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
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卖菜油的老人,他有时不借助于油漏,也能熟练地将油一滴不漏地注入壶口狭小的油壶里,那功夫,真是堪比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
如今,当我驻足凝视老街时,承载我年少记忆的场景大多消逝了。
当年的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曾经高低不一、错落有致、略带古意的房屋均被统一的二层楼房替代了,供销社、电影院、粮站……一个,一个也都不在了,老街变得空空落落的。
天光下,除了几位眼眸浑浊的老人坐在竹椅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话和三三两两骑着电瓶车的过客,很少见到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和追逐打闹的孩子们,他们都去哪里了?往大都市谋生或求学去了吗?现在的老街,已如退了潮的海,不知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繁荣过后的衰退,还是洗净铅华后的内敛?
弹指一挥间,我离开老街已有二十余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我已变成了风霜满面的中年人。
正想着,一抬眼,我已步入二十年前修建的一条与老街交叉连接着的新街。
新街的一头是我年少时的家,另一头是通往远方的站台,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恍惚,不知道该往那个方向去?于是,深深地呼吸一下纯净的空气,定了定神,招了辆的士,从最初出发的地方再次出发,带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回望着老街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一片苍茫之中……
有人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座老房子,或都有一条老街,它们是我们心中无法抹去的梦。
是啊,尽管时光老去,老街也不会成为一幅褪色的照片,尤其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地方,它会一直鲜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时光深处的老街随笔 篇2
他是一个赤脚医生,他真的是“赤脚”的,他从不穿鞋,据说,他是习惯了光脚,穿上鞋就不会走路了。
他不是谁,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四处行医,将家里的农活全部撂下。
所以我们家很穷,每当我抬头,阳光就会从破裂的瓦片缝隙里照射下来,盛满我的小小的瓷饭碗。
我曾问母亲:“我爹怎么不穿鞋啊?”母亲不搭理我,她怨父亲,怨父亲专给人治病,挖草药,而报酬仅仅是一顿饭、一碗酒。
母亲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帮他干农活,照顾孩子。
所以,一提到父亲,母亲就来火。
但父亲的医术倒是真的高明,没有他拿不准的病,没有他挖不到的药,身为儿子,我也因此受益不少。
我生病是不用去医院的,包在父亲身上。
所以有时我很渴望生病,因为这样常常在外面跑的父亲就会回来,陪着我。
我是长到13岁时才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父亲的,我还知道我的父亲在我刚出生没多久就死了,而这个“赤脚”男人,没能医好我父亲。
从此,我开始莫名的恨这个男人。
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再见到他,更不愿意见到他那双丑脚。
我甚至想到了离家出走。
我将他的钱包洗劫一空,然后,坐上了去县城的车。
后来听人说,他在车后面以飞快的速度追我,足足跑了一公里才停下来。
阴差阳错的,那天我没能出走成功,我的钱被小偷扒了,我无家可归,只好蜷缩在车站候车厅的角落里过夜。
而第二天睁开眼睛时,眼前是一双熟悉的脚。
对,是他的脚,只不过,那双脚上,布满了泥浆和血丝,肿得吓人。
他坐在我面前,就那么一直盯着我,直到我泪如雨下。
我偷了他的钱后,他身上没有一分钱了,他是连夜走了几十里路赶到县城的,摔了很多跤。
我不顾一切地扑向他,在他的怀里嚎啕大哭。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天那双血肿的脚。
我也才懂得,“父亲”的含义,是那些撼动不了的慈爱。
他终于告诉我,他当年没能治好我的亲生父亲后,就一直责怪自己,并发誓这辈子都不穿鞋子,以此来惩罚自己。
父亲自今依然不穿鞋,他的脚已经瘦小得不成样子,而且伤痕累累,几乎目不忍视,但对于我来说,那是一双世上最美的脚。
时光深处的老街随笔 篇3
老屋有小院,小院子里曾有一棵杏树,据说是我出生那年种下的。
到我记事的时候,树的枝丫已经遮挡了院子的半边天。
夏天,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时,顶着大“脑袋”的杏树冠像是“遮阳伞”。
站得笔直的树,像条忠厚老实的狗,坚定地把炙热的阳光拒之院外。
我还记得杏花开满枝头的样子,突然间,眼前花儿漫天,路过树下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迈哪只脚,因为怎么迈都可能踩着落在地上的花瓣儿。
我在这颗杏树下,学会了“小心翼翼”。
花落无声胜有声,这大约是生命陨落最沉重的瞬间。
比起杏花儿,我对杏树的叶子要熟悉的多。
杏树的叶,不似桃叶窄细,也不似苹果、樱桃叶小巧,每一片杏叶都肥圆肥圆的,像一个个憨厚的胖小子。
杏叶的表面光滑,好似平静的湖面,这是我最中意的地方。
小的时候,我常常搬来一个小凳子,踮脚、伸手,勾下够得着的枝条,寻找和叶子一样绿的果子。
摘下来,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那酸中的涩,涩中的苦一下子扑到舌头根。
只得紧闭着眼睛,咂摸着舌头,咽下带着苦涩味的口水,偷偷地把剩下的杏子丢掉。
躲在杏叶子后面的.杏子,一天天大起来了。
树顶的杏儿先黄了,心里就有了爬到树上摘的想法。
母亲一定识破我的念头,时时警告说“离树远点”。
杏树上有毛毛虫,那叫“波刺毛”的毛毛虫,身上长满刺,碰到人身上,会起红红的疙瘩,又痒又痛。
站在小平房上,看着远处伸手不能及的红杏,真的就不敢爬上树去摘了。
小学二年级的春天,我们搬去了新房。
夏天要结束,秋天将开始的时候,杏树竟为我们送上一份难得的贺礼。
那年结的杏,比往年都要大,要多。
成熟的杏,黄中带着微红,咬一口,满嘴都是殷实的杏肉,淡淡的酸与清香绕在鼻尖。
有天,是开集日子,母亲起早摘了满满一篮子黄红的杏儿,这一篮子的杏儿是要卖掉的。
摘的时候,她说:“你想吃多少,尽管吃,就是吃多了不好。”我心里嘀咕:“这么好的杏,你就是想卖掉。”
集市上,来卖自家杏子的也有几家。
我有意偷瞄别人家的杏儿,暗自比较,没有一家能与母亲篮子里的杏儿相比。
收摊时,母亲自言自语:“还能卖这么多钱呀。”几十年后,想起那些清苦的日子,发现原来那话里的滋味,要胜过我嘴巴里的杏的酸甜。
后来几年,母亲忙于挣钱无暇打理杏树,父亲怕杏树上的虫子跑到邻居家去“逍遥法外”,他们商量着剪去太茂盛的枝丫,只留下粗粗的枝干和孤零零的几个枝子。
渐渐地,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春天,杏树不再长出新的叶子,枯死在老屋的院子里。
但杏树带给我的恬静与喜悦,依然荡漾在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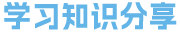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