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儒家思想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重伦理,正名分。伦理是宗法家族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儒家赋予伦理观以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合,既强调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伦理准则,又直接视违背伦理的行为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礼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等级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正名”,就是要通过立法恢复这种等级名分制的权威,使之“名正言顺”,从而保证伦理原则的约束力。孟子也宣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伦的准则。荀子则明确强调“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这种等级制度就是把“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等标志封建主要阶级成分内容纳进礼的内容中来,使得“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礼)为隆正”,并将贯穿着伦理精神的“礼”奉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这种理论经汉代儒家大师董钟舒的加工改造,最终演变为指导古代立法的“三纲五常”。第二,重家国、倡忠孝。儒家发扬了西周礼治秩序中的家庭为本位的传统,重视调整家庭内部关系。孔子一再强调“笃于亲”,认为孝亲是“为仁之本”,百善之先。孟子进一步阐发道:“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儒家不仅视“孝”为伦理的范畴,而且将“孝”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不孝即为严重犯罪,自夏朝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不孝罪”入律,隋唐将“不孝罪”列入“十恶” 大罪。《孝经》宣告:“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儒家倡孝的目的在于移孝忠君,“国之本在家”,父与君是相通的,忠以孝为基础,孝以忠为归宿,通过维护家长制的宗法原则来实现忠君守法,以此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第三,重差等,别贵贱。等级差别是礼的本质特征,主要作用是“承天之道”以 “治人之情”,而“天道”体现的是等级划分,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人不上大夫”,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吏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认为:“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荀子以为:“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由此看来,儒家主张国家法制要以明上下贵贱之分为宗旨,实际上是用法律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二)由“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重视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儒家在继承西周“德”的基础上,又对之进行了改造和补充,将之视为治理国家,取得民众支持的根本途径,这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此外,儒家还抬高了德的地位,置之于国家法律甚至君主个人权力之上,作为区分“仁君”与“暴君”的准绳。当然,儒家的“德治”并不完全否认刑法的功用,其实,儒家和法家一样,都认为刑法是必不可少的统治工具。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才是政刑。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但也重视两者的不同后果,即德治对人心的影响是积极的`,刑罚的后果是消极的,因此,儒家更青睐于德治。
三、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及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古代行为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礼,其内容主要是规定了在等级秩序中人们的义务性规范,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违礼的行为要受到制裁,“出礼则入刑”,这样的制裁既包括道德上的谴责,也包括国家强制力的惩罚,后者则主要是刑、法、律的调整范畴。对于古代法律的把握,只有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考察,才有完整的意义。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实践的总结,“治之经,礼与刑”,礼与刑,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初形式和内容。中国古代法律就是从礼、刑(法)关系的演进中发展而来。
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经历了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过程。夏商周时期礼、法处于分立状态。礼从氏族时期“事神致福”的祭祀仪式,到阶级社会注入尊君的内容, “尊先祖而隆君”,至周更加系统化,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的标准,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根本。“违礼”行为要受到制裁,甚至要处以“刑”的惩罚。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是对立的。春秋时期,出现了“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诸侯争霸局面。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反映在法律意识和法制建设上,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法治国”、“缘法而治”的法家的兴起。管仲率先将国君所立的“法”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从礼中分离出来,树立了“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法治模式。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把法律铸在鼎上,率先公布了成文法,打破了“议事以制”、“刑不可知”的秘密法状态。时至公元前445年,魏相李悝总结各诸侯国的立法经验,编篡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成文法运动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法的核心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旨在打击宗法贵族势力。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儒法两家礼、法之争日益激烈,礼、法关系尖锐对立起来。汉魏以后,礼、法关系又趋于合一。
礼、法作为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尽管存在着对立,但也存在互补的社会调整功能,并非不可调和。儒家坚持礼,主张德治、人治,但并不反对以刑的力量来维护礼。荀子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同时,更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法家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排斥伦理化的礼。商鞅认为“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是“法之常”。所以,“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礼、法关系由对立走向结合成为必然。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在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走向合一,儒、法两家由分离到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秦王朝二世而亡,标志着法家治国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两汉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求助于黄老之术,推行“休养生息”,从原初的以道补法,发展到以儒、法、道三者结合的治世之术,造就“文景之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过于消极的黄老之术越来越不适应传统的专制政治的需要。统治者急需树立一种更能有效维护专制政治的权威思想,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统治,新儒学于是应运而生。
所谓“新儒学”是指西汉硕儒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学思想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新的补充和发展。他对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改造,提出了“天人感应”,将儒家思想推崇为社会、政治乃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同时又吸收法、道、阳阳五行各家及商周以来的天命神权观。还主张“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又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确立了“三纲五常”的绝对准则。从而使儒学发展为一种有利于建立和维护集权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新儒学的政治法律理想迎合了大一统思想统治的要求,所以,汉武帝欣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上升为官学,儒家思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经义也逐渐被法律化,中国古代法律以新儒学的出现为标志而形成。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汉儒以以经注律、以经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四、“春秋决狱”的历史作用
“春秋决狱”这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春秋决狱促进了儒法合流。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董仲舒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将儒家的道德原则引入法律,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儒家从书斋走向实践,从司法领域到立法领域,使儒家思想渗透到整个法律实践活动过程中,儒法两家由对立走向融合。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强调法官在认定犯罪时对行为者的主观因素做深入考察,实际上是从秦汉法律中“客观归罪”的法定精神转向主观归罪,使儒法两家的精神原则在碰撞中交错融合,逐渐走向统一。董仲舒还以春秋决狱的方式恢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从而使儒家经义与法家法典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指导司法审判。儒家的道德精神潜移默化于法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从而为儒家和法家的最终合流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拉开了序幕。
五、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规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诸儒引经注律的热情可见一斑。汉儒极力将儒家学说的精义贯注到法律的每一条,每一字上,力*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这一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即“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强调德治。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展为“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的指导思想,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成为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论依据与主流法律思想。到唐朝,封建传治者总结了汉以来运用礼刑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唐律》还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等封建伦理道德奉为信条,贯彻于法律中。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1)“八议”制度为《曹魏律》首创,是中国封建法律形成的维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诉讼中的法律特权的制度。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晋及南北朝各国修律,一直沿用魏之“八议”。北齐制律时,进一步完善“八议”的内容,规定凡犯有严重危实统治阶级利益的“重罪十条”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2)“八议”入律之后,西晋统治者又规定了“官当”制度。晋律规定免官可当三岁刑。南朝《陈律》正式将“官当”入律,并创立了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官当制度,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但因“公坐、过、误,罚金。”官当制度是“八议”制度的扩大与延伸,其目的在于维护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吏的法定特权。
(3)“晋律”首开以服制论罪的先例,明确提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则。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来规定亲属的范围、等级,亦即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称为“服制”。所谓“五服”就是将服制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度级。亲属相犯是以服制的轻重来确定罪与非罪,或刑罪的轻重。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置愈轻;以卑犯尊,处置愈重。服制愈远:以尊犯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北齐修律时,吸收晋律的立法原则,单修《五服制》一卷,作为刑律的附则,《隋书·经籍志》将其列于刑法部分。“准五服以制罪”正是儒家纲常名教在刑法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礼法合一的特点。法官判案,须先明服纪。从此,历代法律均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4)《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儒家宣扬的纲常伦理道德,核心是维护君权和父权,随后各朝封建法律都把损害君权和父权的犯罪行为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封建政权和封建礼教的十种罪名列为“重罪十条”,置于律首,进一步集中了封建法律的打击目标。这十种罪名是:“一曰反逆(谋危社稷、企*推翻皇帝的统治),二曰大逆(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叛(***投敌),四曰降(投降敌人),五曰恶逆(指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等谋害尊亲属的行为),六曰不道(指残忍酷毒,如杀非死罪家人、肢解人体等),七曰不敬(指对皇帝、家长的各种失礼行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为),九曰不义(指卑下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十曰内乱(指家族内的犯奸行为)犯此十种大罪者,不在八议、赎刑之列,通常是极刑处死。”“重罪十条”进一步把礼与法律结合起来,使法律成为推行礼治的工具。“重罪十条”是我国法律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开皇律》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把其定为“十恶”大罪,并为以后历朝法律所因袭。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之外,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创制了上请原则、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等刑罚适用原则。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1)“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指臣对君、子对父不允许有犯上作乱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无行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汉代其成为决断触犯皇权及皇帝尊严与安全的犯罪的理论根据之一。这一法律观点由儒家尊尊亲亲原则而引伸出来。
(2)罪止其身。指只应当惩罚犯罪者本人,不可惩罚因他人犯罪受牵连的无辜者。而汉武帝时期有族殊连坐,儒生桓宽提出反对意见。“《春秋》有云,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闻恶恶及其人,未闻什伍之相坐。”这里根据《春秋》之义“恶恶及其身”而反对株连父子兄弟、亲戚邻里的法律观点。
(3)“以功覆过”。此论点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汉代春秋决狱者常以此条经义为据,为有功于国者犯罪辩解,使他们免受法律追究。该观点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权,为以后的法定“议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除上述具体法律观点外,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形成了许多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如“亲亲得相首匿”、“原心定罪”、“恕及妇孺”等观点,前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在引经决狱,以经注律过程中形成的儒家法律观点,对历代封建立法、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封建法律的礼、法融合奠定了基础,充实了内容。
4、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汉书·隽不疑传记》记载:西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称卫太子。诏使公卿大臣们辨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臣相御使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有人说:“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逃,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于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大批儒家进入司法机关,并且,在司法队伍中,司法官也迫切需要学习儒家经义以提高儒家素养水平。因此,司法官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儒家化,司法队伍也越来越儒家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实践产生了实际效果。
转载请注明出处记得学习 » 浅谈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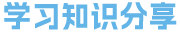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