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卷二十九列传第十九
《南史》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以下是为大家找到的《南史》卷二十九列传第十九,供大家参考。
蔡廓
廓博涉群书,言行以礼,起家着作佐郎。后爲宋武帝太尉参军、中书黄门郎,以方鲠闲素,爲武帝所知。载迁太尉从事中郎,未拜,遭母忧。性至孝,三年不栉沐,殆不胜丧。
宋台建,爲侍中,建议以爲“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从之。
世子左卫率谢灵运辄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纠免官。武帝以廓刚直,补御史中丞。多所纠奏,百僚震肃。时中书令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亮每事谘廓然后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终不爲屈。迁司徒左长史,出爲豫章太守。
征爲吏部尚书。廓因北地傅隆问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纸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言署纸尾也。羡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权要,徙爲祠部尚书。
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难也。”
廓年位并轻,而爲时流所推重,每至岁时,皆束带诣门。奉兄轨如父,家事大小,皆谘而后行,公禄赏赐,一皆入轨,有所资须,悉就典者请焉。从武帝在彭城,妻郗氏书求夏服。廓答书曰:“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时轨爲给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兴宗。
兴宗字兴宗,幼爲父廓所重,谓有己风。与亲故书曰:“小儿四岁,神气似可,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故以兴宗爲之名,以兴宗爲之字。
年十岁丧父,哀毁有异凡童。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以与兄轨。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兴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深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寻又丧母。
少好学,以业尚素立见称,爲中书侍郎。中书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并与之厚善。元凶弑立,僧绰被诛,凶威方盛,亲故莫敢往,兴宗独临哭尽哀。
孝武践阼,累迁尚书吏部郎。时尚书何偃疾患,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便可开门当之,无所让也。”
后拜侍中,每正言得失,无所顾惮。孝武新年拜陵,兴宗负玺陪乘。及还,上欲因以射雉,兴宗正色曰:“今致虔园陵,情敬兼重,从禽犹有馀日,请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车,由是失旨。竟陵王诞据广陵爲逆,事平,孝武舆驾出宣阳门,敕左右文武叫称万岁。兴宗时陪辇,帝顾曰:“卿独不叫?”兴宗从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应涕泣行诛,岂得军中皆称万岁。”帝不悦。
兴宗奉旨慰劳广陵,州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在城内同诛。兴宗至,躬自收殡,致丧还豫章旧墓。上闻谓曰:“卿何敢故尔触网?”兴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杀贼,臣自葬周旋,既犯严制,政当甘于斧钺耳。”帝有惭色。又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锁付甯州,亲戚故人无敢瞻送,兴宗时在直,请急,诣朗别。上知尤怒。坐属疾多日,白衣领职。
后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与丞相义宣同谋。时坦已死,子令孙作山阳郡,自系廷尉。兴宗议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爲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见从。
出爲东阳太守,后爲左户尚书,转掌吏部。时上方盛***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唯兴宗以方直见惮,不被侵媟。尚书仆射顔师伯谓仪曹郎王耽之曰:“蔡尚书常免昵戏,去人实远。”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每至官赌,常在胜朋。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
大明末,前废帝即位,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义恭曰:“建立储副,本爲今日,复安用此?”兴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营阳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书,可检视也。”不从。
时义恭录尚书,受遗辅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归近习。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近远。兴宗职管九流,铨衡所寄,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恇挠,阿顺法兴,恒虑失旨,每闻兴宗言,辄战惧无计。
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征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顔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
兴宗每奏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存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闇,不亲万机,选举密事,多被删改,非复公笔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谢庄等迁授失序,兴宗又欲改爲美选。时薛安都爲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兴宗先选安都爲左卫将军,常侍如故;殷恒爲黄门,领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单爲左卫。兴宗曰:“率、卫相去,几何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则顿爲降贬。若谓安都晚过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轻,宜有选序,谨依选体,非私安都。”义恭曰:“若宫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应侍中,那得爲黄门而已?”兴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实远。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爲少也。”使选令史顔禕之、薛庆先等往复论执,义恭然后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爲右卫,加给事中,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兴宗爲吴郡太守,固辞;又转南东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上表言兴宗之失。诏付外详议,义恭因使尚书令柳元景奏兴宗及尚书袁湣孙私相许与,自相选署,乱群害政,混秽大猷。于是除兴宗新昌太守,郡属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骇。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得。及兴宗被徙,论者并言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
顷之,法兴见杀,尚之被系,义恭、师伯并诛,复起兴宗爲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固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情所见,在内大臣,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难不测,同年而语乎。”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既人不自保,比者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时士庶危惧,衣冠咸欲远徙,后皆流离外难,百不一存。
重除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诣兴宗属事。兴宗谓羡曰:“公关门绝客,以避悠悠之请谒耳,身非有求,何爲见拒?”羡复命,庆之使要兴宗。兴宗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今所忌惮,唯在于公。公威名素着,天下所服,今举朝惶惶,人怀危怖,指撝之日,谁不影从?如其不断,旦暮祸及。仆昔佐贵府,蒙眷异常,故敢尽言,愿思其计。”庆之曰:“仆比日前虑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正当委天任命耳。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虽有其意,事亦无从。”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复要富贵,期功赏,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将帅,正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威风先着,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谁敢不从?仆在尚书中,自当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诸所行造,人间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恶之祸也。且车驾屡幸贵第,酣醉弥留。又闻斥屏左右,独入合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仆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详其祸福。”庆之曰:“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政当抱忠以没耳。”顿之,庆之果以见忌致祸。
时领军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邑里讹言玄谟当建大事,或言已见诛。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兴宗故郡人也,爲玄谟所信,使至兴宗间。兴宗谓曰:“领军比日殊当忧惧。”法荣曰;“顷者殆不复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兴宗因法荣劝玄谟举事。玄谟又使法荣报曰:“此亦未易可行,其当不泄君语。”右卫将军刘道隆爲帝所宠信,专统禁兵,乘舆当夜幸着作佐郎江斅宅,兴宗乘马车从。道隆从车后过,兴宗谓曰:“刘公,比日思一闲写。”道隆深达此旨,掐兴宗手曰:“蔡公勿言。”
时帝每因朝宴,棰殴群臣,自骠骑大将军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湣孙等咸见陵曳,唯兴宗得免。
顷之,明帝定大事。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産、女婿韦希真等曰:“当艰难时,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季産曰:“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非不会机,但大事难行耳。季産言亦何益。”玄谟有惭色。
当明帝起事之夜,废帝横尸太医合口。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景文曰:“此虽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将乘人。”
时诸方并举兵反,朝廷所保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兴宗曰:“宜镇之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上从之。
迁尚书右仆射,寻领卫尉。明帝谓兴宗曰:“顷日人情言何?事当济不?”兴宗曰:“今米甚丰贱,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言既平之后,方当劳圣虑耳。”尚书褚彦回以手板筑兴宗,兴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
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从登南掖门楼以观之。兴宗潸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兴宗始昌县伯,固让,不许,改封乐安县伯,国秩吏力,终以不受。
时殷琰据寿阳爲逆,遣辅国将军刘勉攻围之。四方既平,琰婴城固守。上使中书爲诏譬琰,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顺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今直使中书爲诏,彼必疑非真。”不从。琰得诏,谓刘勉诈造,果不敢降,久乃归顺。
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反,后遣使归款,泰始二年冬,遣镇军将军张永率军迎之。兴宗曰:“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不过须单使一人,咫尺书耳。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爲患不测。”时张永已行,不见信。安都闻大军过淮,果引魏军。永战大败,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见如此。初,永败问至,上在干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兴宗。谓休仁曰:“吾惭蔡仆射。”以败书示兴宗,曰:“我愧卿。”
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吴兴丘珍孙言论常侵兴宗。珍孙子景先人才甚美,兴宗与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阳郡,会晋安王子勋爲逆,转在竟陵,爲吴喜所杀。母老女幼,流离夏口。兴宗至郢州,亲自临哭,致其丧柩,家累皆得东还。
迁会稽太守,领兵置佐,加都督。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兴宗皆以法绳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啓罢省之,并陈原诸逋负,解遣杂役,并见从。三吴旧有乡射礼,元嘉中,羊玄保爲吴郡行之,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
明帝崩,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彦回、中领军刘勉、镇军将军沈攸之同被顾命。以兴宗爲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弘兴宗爲文帝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君不得尔。”弘还,依事啓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至是,兴宗复尔。
道隆等以兴宗强正,不欲使拥兵上流,改爲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拜。
兴宗行己恭恪,光禄大夫北地傅隆与父廓善,兴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孙敬玉尝通兴宗侍儿,被禽反接,兴宗命与杖,敬玉了无怍容。兴宗奇其言对,命释缚,试以伎能,高其笔劄,因以侍儿赐之,爲立室宇,位至尚书右丞。其遏恶扬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
兴宗家行尤谨,奉归宗姑,事寡嫂,养孤兄子,有闻于世。太子左率王锡妻范,聪明妇人也,有才学。书让锡弟僧达曰:“昔谢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其爲世所重如此。
妻刘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觊始生子彖,而妻刘氏亦亡,兴宗姊即觊母也。一孙一侄,躬自抚养,年齿相比,欲爲婚姻,每见兴宗,辄言此意。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姊生平之怀,屡经陈啓。帝答曰:“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旧意既乖,彖亦他娶。甚后彖家好不终,顗又祸败,彖亦沦废当时,孤微理尽。敬猷遇害,兴宗女无子嫠居,名门高胄,多欲结姻。明帝亦敕适谢氏,兴宗并不许,以女适彖。
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遗命薄葬,奉还封爵。追赠后授,子顺固辞不受,又奉表疏十馀上。诏特申其请,以旌克让之风。
初,兴宗爲郢州,府参军彭城顔敬以式卜曰:“亥年当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开府之授,而太岁在亥,果薨于光禄大夫云。文集传于世。
子顺字景玄,方雅有父风,位太尉从事中郎。升明末卒。弟约。约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驸马都尉。仕齐,累迁太子中庶子、领屯骑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约脱武冠解剑,于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赎论。
出爲宜都王冠军长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谓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约曰:“南豫密迩京师,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时诸王行事,多相裁割,约居右任,主佐之间穆如也。
迁司徒左长史。齐明帝爲录尚书辅政,百僚脱屐到席,约蹑屐不改。帝谓江祏曰:“蔡氏是礼度之门,故自可悦。”祏曰:“大将军有揖客,复见于今。”
约好饮酒,夷淡不与世杂。永元二年,卒于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赠太常。弟撙。
撙字景节,少方雅退默,与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齐位给事黄门侍郎。丁母忧,庐于墓侧。齐末多难,服阕,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长史,并不就。
梁台建,爲侍中,迁临海太守。公事左迁太子中庶子,复爲侍中,吴兴太守。初,撙在临海,百姓杨元孙以婢采兰贴与同里黄权,约生子,酬*哺直。权死后,元孙就权妻吴赎婢母子五人,吴背约不还。元孙诉,撙判还本主。吴能爲巫,出入撙内,以金钏赂撙妾,遂改判与吴。元孙挝登闻鼓讼之,爲有司劾。时撙已去郡,虽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钱,及在吴兴,不饮郡井,斋前自种白苋紫茄,以爲常饵,诏褒其清。加信武将军。
时帝将爲昭明太子纳妃,意在谢氏。袁昂曰:“当今贞素简胜,唯有蔡撙。”乃遣吏部尚书徐勉诣之,停车三通不报。勉笑曰:“当须我召也。”遂投刺乃入。
天监九年,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祅道聚衆攻宣城,杀太守朱僧勇,转寇吴兴,吏人并请避之。撙坚守不动,命衆出战,摧破斩承伯,馀*悉平。
累迁吏部尚书,在选弘简有名称。又爲侍中,领秘书监。武帝尝谓曰:“卿门旧尚有堪事者多少?”撙曰:“臣门客沈约、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无人。”约时爲太子少傅,岫爲右卫将军。
撙风骨鲠正,气调英嶷,当朝无所屈让。尝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参掌通署,乃推白牒于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谓举尔所知,许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无烦参掌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尝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驾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寻悔,取事爲画。
帝尝设大臣饼,撙在坐。帝频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饼如故。帝觉其负气,乃改唤蔡尚书,撙始放箸执笏曰:“尔。”帝曰:“卿向何聋,今何聪?”对曰:“臣预爲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帝有惭色。
性甚凝厉,善自居适。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来造谒,往往称疾相闻,间遣之。及其引进,但暄寒而已,此外无复馀言。
后爲中书令,卒于吴郡太守,諡曰康子。司空袁昂尝谓诸宾曰:“自蔡侯卒,不复更见此人。”其爲名辈所知如此。子彦深,宣城内史。彦深弟彦高,给事黄门侍郎。彦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长,博涉经传,有文词,尤工草隶。陈太建元年,累迁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拜驸马都尉、中书侍郎,迁晋陵太守。及将之郡,更令左右修中书廨宇,谓宾友曰:“庶来者无劳。”
寻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时所重,常端坐西斋,自非素贵名流,罕所交接,趣时者多讥焉。宣帝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爲黄门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帝默然而止。肃闻而不平,义兴公主日谮之,寻免官,迁交趾。顷之追还。
后主嗣位,爲给事黄门侍郎。后主尝置酒,欢甚,将移宴弘范宫,衆人咸从,唯凝与袁宪不行。后主曰:“何爲?”凝曰:“长乐尊严,非酒后所过,臣不敢奉诏。”衆人失色。后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后主谓吏部尚书蔡征曰:“蔡凝负地矜才,无所用也。”寻迁信威晋熙王府长史,郁郁不得志。乃喟然叹曰:“天道有废兴,夫子云'乐天知命',斯理庶几可达。”因着小室赋以见志。陈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颇知名。
论曰:蔡廓体业弘正,风格峻举。兴宗出内所践,不陨家声。位在具臣,而情怀伊、霍,仁者有勇,验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风素气,无乏于时,其所以取贵,不徒然矣。至于矜倨之失,盖其风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的主要内容:
《南史》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便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练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
《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
影响与价值:
1、立足民族融合
李氏父子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决心写一部体现“天下一家亲”贯通南北朝的史书,参考”杂史”千余卷,删繁就简,事增文省,其中删《魏书》《宋书》最多,删文多为诏诰、符檄、章表。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虏”、”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2、文字简明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3、不足之处
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以王、谢等大家为主,《列传》多附传,附传的人物多属家族成员,例如《南史·袁湛传》附传人物达12人,《北史·陆俟传》附传多至20人,前后相去百余年,乃至于有大量的神怪迷信,王鸣盛批此甚谬妄。《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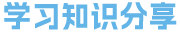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