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思想中的异托邦解读论文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说到论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论文该怎么写吗?以下是精心整理的福柯思想中的异托邦解读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因为深深处于与所谓的正常人不同的基本生存塑形和情境之中,福柯①才会从个人的异样本欲中,建构出我们无法触及的那部分真实生活存在场域和异质性思境。他将自己这种独特的异常研究方式指认为尼采式的谱系学。并且,他的谱系学研究真正对象之一,是现实存在中作为另类或者他性空间物的异托邦。这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生成的一个重要的反向存在论观念,即通过指认一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他性物和非常事件,这些他性存在本身就是要解构现实体制的合法性。
这种他性存在被福柯命名为异托邦(hétérotopie),以区别于非现实的理想悬设物———乌托邦。
章节一
青年福柯最早是在《词与物》一书中,在常识的意义上提到谱系学问题的。在那里,谱系学是指传统生物学的物种连续性谱系树和分类谱系研究。1971年,在一本纪念伊波利特的文集中,福柯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学》(Nietzsche,lagénéalogie,l?histoire)。此文是他专门解读尼采的谱系学的研究性论文。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提炼和系统概括出一种与传统历史学根本对立的重构历史的谱系研究方法,即拒斥起源、否定总体历史线性发展、复归历史细节的真实谱系的效果史观。由此,他也第一次标识出谱系研究是继考古学之后自己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式补充。
找到没有本质的事物,也就是找到历史中的他者———这是一种将传统生物树式谱系链斩断后生成的新的谱系真相,尼采就是在这个全新的倒置构境层中透视传统道德和重估一切文化价值的。
正是在这个传统谱系倒序的构境意义域中,福柯深入地发展了尼采这种新的倒置的谱系观念。他提出,谱系研究就是要重新面对那些被总体性历史棱镜剔除的黑暗中的独特事物和现象,让它们重现,即不再是某个重大历史目的和伟大进步目标的“阶段性”事件和“不成熟”的雏形,它们只是无本质的自己,即非目的论中的历史他者,这也就是反对起源的谱系研究的真正历史对象。并且,他的谱系学研究真正对象之一,是现实存在中作为另类或者他性空间物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
其实,这个被福柯重新构境为异托邦的“hétérotopie”一词,在法文中起先是在福柯十分熟悉的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使用的,它是指与动植物原位移植相对的不同部位的器官和组织移植,所以也称异位(移植)。福柯第一次在异境中使用此词是在1966年的《词与物》的“序言”中。在那里,福柯已经跳出此词的原初语义构境,而直接与乌托邦概念相对完全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情境,即作为他性实有空间的异托邦构境。
在此,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词与物》“序言”中福柯那个著名的大笑场景。福柯之笑,在于他看到博尔赫斯书中提及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里的另类动物分类,认为这种奇怪的分类(不是同一性的构序)解构了传统西方文化对存在本身的命名(分类)之有序,仍然陷在多样性感性事件中的“皇帝所有”、“有香味的”、“驯服的”、“传说中的”、“数不清的”、“刚刚打破水罐的”等等的动物区分,相对于西方古典认识型中对自然历史和物种分类学命名的同一性构序,反向呈现了“丧失了场所和名称‘共有’的东西”,它们并没有被摆置到同一性理性逻辑的共同场所。开心的福柯说,这种来自于现实异域(中国)的他性分类法“导致了一种没有空间的思想,没有家园(feu)和场所的词与范畴”,这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固有分类秩序则是扰乱人心的无序性。如果说,西方的同一性理性逻辑的分类是文化自我安慰式的乌托邦,那么来自中国这种他性的无序“分类”就是异托邦(hétérotopie):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它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命名这和那(cecietcela),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是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syntaxe)。……异托邦(诸如我们通常在博尔赫斯那里发现的那些异托邦)使语言枯竭,使词停滞于自身,并怀疑语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异托邦解开了我们的神话,并使我们的语句的抒情性枯燥无味。[1]
可以看出,在《词与物》的“序言”中,福柯的异托邦只是一种打乱西方文化认识型中的词对物构序的异域和外部,它破坏了词语构序的共同场所,解构了建构有序性的句法结构。异托邦即是现实中存在的祛序。不过,那时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显然还没有上升为一个方***范式。不久,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章节二
1967年3月14日,福柯在法国建筑研究会上作了题为“他性空间”(Desespacesautres)的讲演。[2]
正是在这一演讲中,福柯系统阐述了他关于异托邦的全新看法。这一次,他还是从乌托邦为反向参照开始自己对异托邦的精心设定。依他的解释,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lieuréel)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inversée)类似的总的关系(rapportgénéral)的地方。这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irréels)空间。[2]
这是对的。乌托邦总是某种针对现实存在中并不存在的美好的理想悬设,有如中国的“大同世界”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有之乡”。乌托邦总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光亮彼岸世界的引领。福柯认为,异托邦则与乌托邦不同,异托邦不是彼岸世界,它就客观存在于此岸的某处,异托邦恰恰是有真实地点和空间存在的场所,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一些真实的场所(deslieuxréels)———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contre—emplacements)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实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2]显然,与《词与物》中的异托邦概念相比,福柯在这里已经在生成一种新的批判性构境范式,异托邦被界定为与没有真实场所的乌托邦相反的现实存在的东西,但这些真实存在却时时通过自己的存在反对和消解现实,甚至说,异托邦就是现实的颠倒性存在,对现实形成危险的一种他性空间(espacesautres)。这里有一个典型的福柯自己的例子,即美国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对于“同志”的他来讲,这种他性空间中的实存正是建构了一种反抗现实异性恋体制的“异托邦”(heterotopia)。
福柯于1975年首次造访旧金山海湾区(BayArea),他本是去柏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但他的同性恋同事们很快就把他带到旧金山的卡斯特罗街和佛索姆区。此后,福柯在1979年、1980年和1983年春重返加利福尼亚,通常都是白天在柏克利活动,晚上去旧金山过夜。在这个反对现实的异托邦狂欢中,福柯的代价是染上了致命的艾滋病毒。
为了进一步说明异托邦与乌托邦的异质性,福柯还专门举了一个例子,即介于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的双重性关系建构的镜像空间。福柯说:镜子(miroir)毕竟是一个乌托邦(utopie),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unlieusanslieu)。在镜子中,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那里却没有我,在一个事实上展现于外表后面的不真实的空间(espaceirréel)中,我在我没有在的`那边,一种阴影给我带来了自己的可见性,使我能够在那边看到我自己,而我并非在那边:镜子的乌托邦。但是在镜子确实存在(existeréellement)的范围内,在我占据的地方,镜子有一种反作用的(retour)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异托邦;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可以说由镜子他性的(l?autre)虚拟的空间(espacevirtuel)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reconstituer)自己;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2]
这是福柯关于异托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说明,并且,此处的阐释显然借用了拉康的镜像理论中的小他者I(a1)的投射关系。在与福柯的关系中,自然是拉康影响了福柯。在1953年前后,福柯几乎每周都去参加拉康在圣安娜医院举办的研讨会。在拉康的镜像说中,当6到18个月大的幼儿(尚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碎裂身体)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统一影像时,即产生了一种完形的格式塔*景。这个完形的本质是想象性的认同关系,并且这还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另一个自我意识,而是“我”的另一个影像。乍一开始,“它的对方”就变成了它的影像———幻象。旋即,他将这*景误认为是自己,此时发生的恰恰是弗洛伊德所讲的那个自恋阶段中自居(认同)关系的幻象化,在拉康的语境中,它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误指(méconnaissance)关系。[3]
这里在对异托邦的说明中,福柯也以镜子为例。首先,我站在镜子前,却在镜像中那个并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看到自己,那个自己虽然不是真实的,可它却让我真地看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格式塔式的完形乌托邦;其次,在我现实存在的身体上,我无法直接看到自己(面容),我只能在镜像这一他性虚拟空间中重新建构自己的形象,所以,镜像同时又承担了异托邦的作用。真实,总是通过虚拟的他性空间反向建构起来。
这也就是异托邦的深层构境意义。
章节三
实际上,在福柯对异托邦的空间设置上,我们不难发现他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空间讨论域。
首先,在福柯看来,与中世纪那种天堂与地狱、圣地与俗物空间之类的等级化的定位空间不同,从17世纪起,伽利略就用广延性代替了等级定位。今天,关系性建构起来的生存性位置又代替了广延性。所以,有真实场所的异托邦的空间并非仅仅指物理意义上的三维存在,而已经在转型为一种人们生存活动的“关系集合”(ensemblederelations),“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emplacementsirréductibles)并且绝对不可迭合(nonsuperposables)的位置”[2]。这也就是说,作为他性空间的异托邦是一种社会生活“关系网”(réseauderelations)式的关系构式物。这也是列菲伏尔开创的空间生产的思路。其实,在福柯看来,今天的整个“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2]。而异托邦则是这种关系网存在中的他性建构物。
其次,依循巴什拉和现象学开辟的道路,“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的空间(espacehomogèneetvide)中,正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各种性质,一个可能同样被幻觉所萦绕着的空间中”。[2]
这也意味着,异托邦恰恰是建构非同质性空间的“外部空间”(l?espacedudehors)。这是布朗肖的话语。异托邦即异质空间,或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ensemblederelations)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2]
福柯的异托邦就是现实存在的外部和他处。
其三,异托邦往往会“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并且,异托邦也会把时间的片断相结合,生成所谓的异托时(hétérochronies)。[2]福柯真是会顺势造新词。
显然,这是空间性的异托邦范式在时间中的他性挪用。这里的时间恰恰是共时性的另类杂合,其作用正是解构总体性的线性时间。对此,福柯举的例子竟然是博物馆和*书馆,因为在这里:在一个场所,包含所有时间、所有时代、所有形式、所有爱好的愿望,组成一个所有时间的场所,这个场所本身即在时间之外,是时间所无法啮蚀的,在一个不动的地方,如此组成对于时间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无定限的积累的计划,好吧,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现代特色。博物馆和*书馆是为19世纪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异托邦。[2]
其四,“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espaced?illusion)的作用,这个幻象空间显露出全部真实空间简直更加虚幻,显露出所有在其中人类生活被隔开的场所”。[2]这里的幻象并非是在贬义构境层上使用的,异托邦的幻象恰恰是对现实存在进行的谱系性的照妖镜像。
然而,福柯告诉我们,在传统所有的文化和历史研究中,异托邦都是处于黑暗之中的,而他的谱系研究就是要让异托邦式的他性空间和时间中的另类事件(“异托时”)得以呈现。他具体指认到,异托邦的第一种形式是危机异托邦:在“原始”的社会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危机异托邦(hétérotopiesdecrise)的异托邦形式,也就是说有一些享有特权的、神圣的、禁止别人入内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留给那些与社会相比,在他们所生活的人类中,处于危机状态的个人的,青少年、月经期的妇女、产妇、老人等。[2]
对此,他举的例子是“走婚”现象。这是指一个一直保持到20世纪还存在的现象,即“年轻的女孩能够不在任何地点失去童贞,在此时,火车,走婚的旅馆,正是这个没有地点的地点,这是没有地理标志的异托邦”。[2]真亏福柯能想得出这样的例证。“失处”不在固定的空间中,而在一个随时运动和变换“没有地点的地点”———异托邦中。不过,这种所谓的危机异托邦到现代已经逐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异托邦的第二种形式:偏离异托邦的异托邦。在福柯看来: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这些是休息的房屋,精神病诊所;当然这些也是监狱。除此以外,无疑还应该有养老院,可以说养老院处于危机和偏离异托邦的边缘。[2]
依福柯这里的表征,这种偏离异托邦的异托邦都是一些人们正常生活空间以外的边缘化场所,也是他真正关心的另类生存场所。再往今天走,福柯举的例子开始出现了公墓、电影院、花园,甚至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说实话,我并不认为福柯所指认的这些历史现象能够完整地说明他关于异托邦的观点。可能也是这一原因,福柯后来并没有强化和泛化这个异托邦的观点,他自己也很少提及这一发明。然而,福柯的异托邦的范式却在后来的空间理论和批判性都市研究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和深化。
比如当代空间研究的思想家哈维对福柯异托邦概念的评论为:福柯“运用它来逃避那个限制人们想象力的规范和结构的社会(顺便提一句,包括他自己的反人本主义),而且通过对空间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其异质性的理解来确认差异、变化性和‘他者’可能活跃或(如建筑师)真正被构造其中的空间”。[4]
这基本上是对的。在哈维看来,福柯的异托邦:加强了空间游戏的共时性这种概念,该观念突出选择、多样性和差异。它使我们能够把城市空间中(有趣的是,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的名单中包含了诸如墓地、殖民地、监狱这些空间)发生的多种异常和越轨行为和政治活动看作是对某种权力的有效且具有潜在意义的重新主张,它要求以不同的形式来塑造城市。[4]179哈维认为,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让我们注意到“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在现实存在的异托邦空间中,“‘他性’、变易性和替代方案可以不被当作纯粹虚构的事物来研究,而是通过与已经存在的社会过程的联系来研究,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些空间内形成,而且对现存规范和过程的批判正是从这里出发才能够特别地有效”[4]179。哈维的诠释构境显然是精致准确的,有助于我们进入福柯这种怪怪的异托邦构境。
参考文献:
[1]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
[2]福柯.他性空间[M].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52-57.
[3]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三章.
[4]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8-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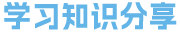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