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汀烟雨杏花寒散文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看过一些经典的散文吧?散文常用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散文要怎么写吗?以下是收集整理的一汀烟雨杏花寒散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傍晚时分,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尽管三月份,还是有点"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的味儿。推开窗子,雨便细丝游龙般地飘落进来,虽然零零星星的,却依旧带来了掩面而来的初春,羞答答地。那种气息,挟着着泥土的清香,蕴含着迎春的淡雅,极像故乡那沾衣欲湿的杏花雨。
故乡的三月和这儿的也没什么大的不同,只不过有了随处可见杏花,低矮不一草蔓滋生的山丘,记忆多了些停留之处,所以稍微闲适时便会旁逸斜出。
在故乡,每当杏花开放,燕语呢喃时,农活也之间多了起来,趁着刚刚化冻的东田尚且松软,麦子返青,村里人会去麦田除草,或是整饬田畦。天气好的时候,没人照看的小孩子有时也会被大人一块带去,放在田间地头,就像是放养的小羊羔或牛犊。乡下人没城里人那么娇气,孩子磕磕碰碰的抚摸几下就好,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倒是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让我至今对家乡的山峁、土洼愈倍觉亲切。
从蹒跚学步到上小学期间,我跟着父母就经常下地,少小时带着妹妹去畦边的荆棘丛中找鸟蛋,稍大些时便和妹妹一块去打猪草。在初春里,若是赶上个艳阳天,最好的去处便是出村二三里地的那片杏林了。
那片杏林,说大也不大,就七八颗杏子树,可毕竟是受到了山沟捧出来的小溪的滋润,于是便有了生机。每年在二、三月间栉风沐雨之后,就会肆意***成一片花的海洋,煞是好看,会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有那么几年,甚至有些养蜂人会过来住段时间。只不过,村里的大人们却很少去,他们说那几颗杏树开出的花煞白煞白的,不只是什么颜色,邪乎!
可孩子们没谁会在乎,因为那片杏林是杏子家的,杏子娘死得早,爹是个哑巴,人很是本分地道。除了不会说话外样样皆通,完全算得上当地的一个能人。杏子姐大概因为亲戚邻居好心人的帮助,不仅说起话口齿清晰,心灵手巧,聪颖伶俐,而且做的一手好针线,深的村里人的喜爱。然而由于家境不好,早早就辍了学。
春风细微,花香阵阵,打猪草的孩子孩子们打满了笼子之后,往往会在杏林里嬉戏玩耍。当我们三五一群,七八一伙地藏猫猫,抓五子,比爬树时,杏子姐先是站在自家院里看着,然后也就过来一块儿玩了。杏子姐姐会玩的花样多,还时而不时地给我们带一些杏干、红枣、柿饼吃,有时候甚至也会帮我们打猪草。
我曾疑心杏子姐在家里怎样跟她哪呀巴爹说话的,便偷偷尾随着去她家看个究竟,可每次总是会被撵了回来。一来二去,我觉着杏子姐有点不大气,便打算不再搭理她。可杏子姐好像也不在乎,只是每次会偷偷地多分我一些她从家带来的干果,于是慢慢地我就不再记恨,原本的那种好奇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淡了。
我上高中那年,杏子姐嫁了人,起初婆婆家倒是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可因为她一直没有怀上身子,被认为是“石女子”,后来就离了婚。从此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呆在娘家照顾哑巴爹,沉默寡言取代了以前的开朗随和,容颜也随着这场婚姻的变故不再姣好如前。
我上大学期间,杏子姐又嫁了一次人,婆婆家家境还说的过去,夫妻也挺恩爱,而且也怀上了孩子。这按理说是好事,可谁知从此好像如同魔咒加身,杏子经常性地遭到丈夫的'毒打,有几次甚至被折磨地死去活来。
村里人说,杏子姐离婚是因为婆家认为她不能生养;带着身子被打是因为她的第二个男人没男人的本事,认为杏子怀的是别人的种。“娘家人不行,弄啥啥不成”。任凭杏子姐千般解释,婆婆家楞是不信。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坯子就这样给毁了。
后来,事实证明:她的第一个丈夫不是男人;第二个丈夫自认为有问题,而实质是个小男人,心理有毛病。而且等这一切水落石出时,杏子的坟头已经长满草蔓,灌木丛生了。杏子姐正是因了这样两个男人,才变得终日郁郁寡欢,精神恍惚,最终带着尚未谋面的孩子难产死在了自家的土炕上。
杏子姐去了,就埋在那片杏林的侧边,斜对着那片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林子。因为有了坟茔,自那以后孩子们就很少去哪里了,于是,那篇杏林慢慢地杂草丛生,荒芜了起来。原有的几棵杏子相继老去,渐渐地风斫雨蚀,只剩下光秃秃几个树桩。林边那条小溪也日渐干涸,以至于断了流。于是好好的一片林子至今只剩下几丛乱草,一冢孤坟,历数着几多星移斗转与冬去春来。
每年清明节,杏子的哑巴爹都会给女儿去上坟。杏子的夭亡让杏子爹已经不再那么精明,完全磊落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糟老头子。木讷、迟钝,不修边幅,依靠村里发的五保津贴度日如年。村里好心的大娘时而会帮他做些针线或救济一些,却再也唤不回他原本的心气,拂不去他失去爱女的心伤。大雪封山的那一年,杏子爹自缢在了那片杏林里。
冬去春来,雁去雁回,杂花生树,蜂蝶纷飞,好一副人间春景!只不过,没有了那片曾经葳蕤恣睢的杏树林,没有了那条曾经淙淙叮叮的细溪,就连杏子爹自缢的那棵树桩也再一次山火中化为了灰烬。人们在路过那片曾经的杏林,总是会驻足凝思:多好的一片杏树林啊!怎么就没了哪?
我曾多次寻觅过那片树林,却每次都怅然而归。在梦境里,我翻越过千山万水去追寻它的踪迹,却每次都在潸然垂泪中醒来,面对的是沉沉深夜与他乡月明。在闲暇时,我翻看童年的旧照片,儿时玩伴会悉数在脑海中浮现,在峭风冷雨中诠释着物是人非和沧桑变迁,却唯有一张面孔定格于记忆深处难于抹去。
早燕暮归,乡野春寒,一汀烟雨,几处妖娆?待铅华洗尽,乱花迷人处一树杏花已卓然于枝头,在峭风冷雨中,在乱草萋萋的旷野中绽放。那一树芳菲,白非真白,红不若红,随着晚风摇曳着,抖落着,朦朦朦胧胧,点点斑斑地溶了。不知是这种色调是它没入到了夜色中,还是披上了一层冷月。
有时候,我寻思着,那该不会是小说常常提及的鱼肚白的颜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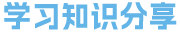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