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道情散文
天水是我心底一个谜,总想知道它的一切。
我和天水是有些历史脉流,祖父就是从天水附近的某个小山村,沿着取经路,逃荒到了唐僧晒经的地儿住脚,萌根生发。
我家的饭食口味就带有天水酸辣味道。小时候母亲常给家里人做荞麦凉粉。记得暑夏酷热难当时,母亲前一天晚上,挖出两碗荞麦珍子,拌入凉水,然后拿到案板上反复揉搓成团,放进盆里,搁置在院子的石几上,笼上罩,醒一夜。第二天清晨,母亲把箩置于锅上,,把荞麦团放入锅内,倒水不停搅拌,沉淀、加热、搅拌成搅团,放凉,既成。家里其他人喜欢用搂子搂成长丝,放盐、醋、糖、酱油、葱姜蒜、辣椒油、花椒粉、加黄瓜丝绿叶菜吃,这滋味真是十足。我最喜欢吃荞麦呱呱,倒出一碗坨,用刀细细切成条,盛在细瓷白碗里,坐在镜子前,脚搭放在沙发上,一根一根地慢吞。那时家的味道还是很浓烈的。我知这是天水的口味基因,对天水的深情是没来由的。
路过天水也有三次,每次遇见仿佛是梦里曾来过。记得第一次是去兰州,路过天水。春明景和的四月二十,望着车窗外仍是初春的害羞模样,没种稼穑的地湿漉漉的绵软,菜花黄,麦苗青。隘畔上的草初芽,柳丝刚柔软飘逸,桃花红了人家农房的一角,陇上江南。
我的家在通天河畔。那年游通天河源头,登上源头峰顶,下望有一小镇,有人告诉我那就是麦积镇,你这一脚迈过去,就是天水市。我难以置信,离自己很遥远又长思量的地是如此迫近,咫尺之邻。
出了天水,才知道天底下还有这般的山。山脉纵横,山莽莽,孤峰兀立而又乱山重叠,线条曲尽,黄土梁峁高耸,沟壑深纵。才知世间竟有如此的沧桑,如此绵长的历史痕。
说来也怪,一直叨念天水,却没有机缘走进这个城市。今年元旦专意去天水。天一直干燥,渴盼瑞雪的飞扬。出宝鸡,天多云,黑色间夹着湖蓝。车向西,到了麦积地界,路边就有了波浪雪线。到了麦积山,雪纷纷攘攘,雾迷迷濛濛,世间尽罩仙露,甘霖湿润朝拜路,宝刹佛境尽显灵性。这样的天真应该游人络绎,实是游客稀拉,真是辜负了酝酿了好几天的雪天。
麦积山在甘肃省的西南部,与宝鸡一衣带水,同属秦岭山系,滋养这里的人们仍是黄河的支流渭河。这里是秦人的发祥地,秦人的祖先曾在这里养马壮大,然后进入陕地。
我对于佛像没有什么研究,无法从艺术的角度去观赏品鉴,我们只是带着一颗好奇之心,去瞻仰那千年之前迷人的容颜。麦积石窟窟龛凿于高20—80米,宽200米垂直崖面上,大多以魏晋作品为主。他们从墙面浮出,饱满丰实,色彩虽经千年的`风蚀,仍然不失其瑰丽的颜色。细瞧塑像,只见他们淡烟细长平眉,圆长脸,厚嘴唇,粗腰高个,极有生活情态。他们不同于龙门石窟雕塑,没有起舞的衣带,长飘的水袖,他们穿的是宽衣大袖,衣襟褶皱如行云流水,翘着大手兰花指。这些佛像秀骨清俊,温婉淳厚。虽是穿着宗教的衣钵,但我觉得更像凡人,他们凝思定目,仿佛每个雕塑都有自己内心故事。这里没有宗教的神秘,却有着对人生荣辱的淡忘和超脱世俗之后的潇洒与轻松。游完麦积山,车拐入了天水市,所遇路人,皆细长眉,厚嘴唇,高颧骨,脸色白皙赤红,乌发如波。原来这麦积雕塑和天水人是一脉。
穿城而过的藉河已封冻,青青的坚冰在阳光照耀,凌冽剔透。料峭的寒风也难掩其清水灵秀。藉河是天水母亲河,在北道注入渭河,(早就有所闻北道,不知何故?原来如此。)藉河是由许多条小溪汇聚而成,它的全境都在天水市境内,涓涓细流成就煌煌大城。藉河千年从李广的衣冠冢下流过,杜甫的长歌短吟更是伴着藉河,从唐朝一直走到今天。李白、李世民、上官婉儿……这些历史名人让这座陌生而又熟悉的家乡亲切了它的面容。繁衍于此的人们,根植于此的文明,流淌于此的历史,更使天水意蕴深沉无限。
这次短暂的驻足,不足以知晓天水。那就让心永远怀着无尽的崇敬与向往去想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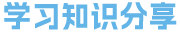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