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经简介
《涅盘经》是佛教经典。又称《大般涅盘经》、《大涅盘经》。中国北凉昙无谶译。40卷,13品。经中说佛身常住不灭,涅盘常乐我净;宣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思想。为大乘佛教前期作品,约于2~3世纪时成书。晋宋时对中国佛学界影响很大,为涅盘学派的本据经典。
涅槃经禅宗思想
中国禅宗思想的两大重要源头是般若思想和涅盘思想。般若之学自东汉传入东土以来,译经事业蓬勃发展,随着般若类经典的旧译臻于完善,经义研究的热潮也随之掀起,晋宋之际讲解般若蔚然成风。最能体现般若特色的佛经是《心经》、《金刚经》,它破除外相、破除非相,乃至于破除“佛法”,以臻于无住生心的境界。禅门在传灯接棒之时,以之作为无上法宝。惠能因听诵《金刚经》而出家求法,后来得五祖亲授《金刚经》要旨而豁然见性,成为禅宗六祖,可见般若思想对禅宗影响之巨。但是,般若类经典讲空固然能使人生起对俗界的厌弃,却难免使人生的追求与期望无所栖泊,而生起茫然失落之感。因此在“色即是空”的后面,还必须下一转语,这就是“空即是色”。
涅盘之学正是侧重于妙有的理论。从大乘思想的发展看,《涅盘经》出现在般若、法华、华严等大品类经之后,也就是说,大乘“空”的思想出现在前,大乘“有”的思想出现在后,从真空到妙有是大乘佛教发展的两个阶段。《涅盘经》是阐释妙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经典,由于此“有”不是对立的现象之有,故称“妙有”。虽然般若明无我,涅盘示真我,般若述凡夫四大假和合,涅盘说一切众生有佛性,二说似多相矛盾,然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般若》、《涅盘》,经虽非一,理无二致。《般若》破斥执相,《涅盘》扫除八倒。《般若》之遮诠,即以表《涅盘》之真际。明乎《般若》实相义者,始可与言《涅盘》佛性义。”正是般若“真空”与涅盘“妙有”的完美融合,才使佛法成为圆满的体系。
《涅盘经》全称《大般涅盘经》,是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典之一。《大般涅盘经》,40卷,北凉昙无谶译,大正藏第12册。本书所论即主要依据此本。 “大般涅盘”是本经特别彰显的名相,它含具法身、般若、解脱的佛之三德,代表着大乘佛教的真实理想。从经文中看,大般涅盘是渊深如海的大寂禅定,如同夏日般光明璀璨,绝对永恒无有变易,怜爱众生犹如父母,济度痴迷出离生死,不生不灭无穷无尽,是超出世俗的宁静、光明、永恒、慈慧、超越的解脱的境界。《涅盘经》经于北凉玄始十年421由昙无谶译出,现编为40卷。由于它的来源和内容都比较复杂,有的学者考证它曾经有过大约七次或八次的增编,以致于在内容上甚至是在涅盘的定义上都产生了矛盾;有的学者甚至推测它并非出于一时一地一个教派之手,而可能是曾经分别流传于我国广大西北地区的多种小本经的合本。
《涅盘经》中如来藏学说中蕴含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皆得成佛、涅盘具常乐我净四德等旗帜鲜明震聋发聩的主张,以及对本心迷失的哲学思索、中道思想、涅盘境界,成为禅宗思想的灵性源头。禅宗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深受涅盘妙有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生命体悟。作为禅宗思想、禅悟思维载体的禅宗诗歌,通过生动形象的吟咏,创造出流漾着涅盘慧光的文学意象,构成了一幅幅彰显著涅盘诗思的意境。《涅盘经》通过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为中国禅林诗苑增添了高华深邃、灵动空明的篇章。
拓展阅读:《涅槃经》与涅槃学派
涅槃学派是指在南北朝形成的以研习、弘传《大涅槃经》为主的佛教思想流派,其研习者史籍中称之为涅槃师。
相传在昙无谶译出《大涅槃经》前,东汉支娄迦谶就译有《梵般泥洹经》二卷,三国魏安法贤译有《大般涅槃经》二卷,吴支谦译有《大般泥洹经》二卷,均早佚。法显在中印度华氏城写得《大般涅槃经》初分的梵本,返国后,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在建康道场寺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世称六卷《泥洹》,相当于北凉昙无谶译的前十卷。中印度昙无谶(385—433)于玄始三年(414年),在北凉译出自己带来的《大涅槃经》初分十卷,当时河西的义学名僧慧嵩、道朗都列席译场笔受;继而又传译在于阗寻得的中分、后分,到玄始十年(421年)译讫,前后共成四十卷十三品,世称大本《涅槃》。北凉译本于宋元嘉年中(424—443年)传到江南,“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宋文帝令义学名僧慧严(363—443年)、慧观(383—453年)及文学家谢灵运(385—433年)等依六卷《泥洹》增加品目、修改文字,删订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世称南本《涅槃》,而以北凉原译四十卷本为北本《涅槃》。《大涅槃经》全经分《寿命》、《金刚身》、《名字功德》、《如来性》、《一切大众所问》、《现病》、《圣行》、《梵行》、《婴儿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师子吼菩萨》、《迦叶菩萨》、《憍陈如》等十三品,主要阐述“佛身常住不灭”、“涅槃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及一阐提和声闻、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佛教思想。
此经在印度本土似乎不很流传,传入中国后,影响却十分巨大。早在五世纪间,昙无谶译出此经时,这一“常乐我净”、“阐提成佛”的学说使当时参加译场的“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而昙无谶“临机释滞,未尝留碍”。特别是,此经传入宋地以前,竺道生依据法显所译的六卷《泥洹经》,就理解到一阐提人可能成佛,发表阐提成佛说,给江南佛教界以极大震动。后来凉译大本传到宋京,果如道生所说。当时竟至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僧嵩非难因而舌烂”的传说,这都反映出此经震动当时佛教界而获得重视的情形。和他同出罗什门下的慧观,著论主张渐悟,并创立“二教”、“五时”的教判,以《涅槃经》为第五时常住教。慧观又继昙无谶的遗志,请高昌沙门道普西行寻求《涅槃》后分(见《出三藏记集》〈昙无谶传〉)。由于这些努力,慧观得以与道生并为涅槃师中两大系。另在凉州方面,曾经亲助昙无谶译此经典的河西道朗撰制了经序,并著《涅槃义疏》释佛性义,为以后诸师讲说此经所依据。与此同时,笔受者智嵩也著有《涅槃义记》,并在凉地讲授,辩论深义。此经传入建业后,更经慧严、慧观、谢灵运等加以再治,称为南本,南北各地弘传更广。
《涅槃经》的中心教义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见本经〈狮子吼菩萨品〉),而涅槃师的.学说即以阐发这一教义为宗要。道生以后,佛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综合言之,其焦点有二:其一,何为正因佛性?其二,佛性为本有还是始有?正因佛性指成佛的内在的、决定性的根据,与此相对而有缘因——即成佛的外在根据或条件。本有、始有之论探讨的是佛性乃先天本具抑或修行始得的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异见叠出,根源于对佛性本体的.不同理解。以下从“正因佛性”、“本有始有”以及“判教”等三方面来论说涅槃学派的思想。
隋吉藏《大乘玄论》中列有十二家关于正因佛性的见解,慧均《四论玄义》卷七中记为根本之说三家、枝末之说十家,共计十三家。二人所载,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倒是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将此十二家分成四类:“然十一家,大明不出三意。何者?第一家以‘众生’为正因,第二以‘六法’为正因,此之两释,不出假实二义,明‘众生’即是假人,‘六法’即是五阴及假人也。次以‘心’为正因及‘冥传不朽’、‘避苦求乐’及以‘真神’、‘阿黎耶识’,此之五解,虽复体用、真伪不同,并以‘心识’为正因也。次有‘当果’与‘得佛理’及以‘真谛’、‘第一义空’,此四之家,并以‘理’为正因也。”此引文只提到三类。除此之外,吉藏将他所赞成的以“中道”为正因佛性列为第四类。依照现行标准,“中道”之见可归于第三类。因此,我们在此仍以三类观之,且“假实”、心识及“理体”之名命名。
“假实”者,包含两种见解:一是“众生”为正因佛性,二是“六法”为正因佛性。《四论玄义》卷七言:“众生为正因体,何者?众生之用总御心法,众生之义,言其处处受生。今说御心之主,能成大觉。大觉因中,生生流转,心获湛然,故谓众生为正因,是得佛之本。”这是照搬《大涅槃经》的一种说法,但解释得很含混。联系其“众生之用”、“众生之义”能御心法及受生流转而言,似乎以众生的主体性作正因佛性。然众生仍属有为、无常法,并不能承担佛性本体之任,因此,其说难以圆通。所谓“六法为正因佛性”者,“六法”指色、受、想、行、识五蕴以及由此五蕴合成的“假人”。相对而言,五蕴为“实有”,故称为“实”。说六法为正因佛性,实际侧重于说众生是佛性,然而众生又不同于木石草壁瓦,“众生心识相续不断,终成大圣。今形彼无识,故言众生有佛性也。”此见解将众生分成“体”、“用”两方面,以“心识为正因体”,有情众生的躯体(即五蕴和合)为其作用。这一说法,亦未能契佛性义之肯綮。
以“心识”为正因佛性者,包括以“心”、“真神”、“心上冥传不朽之义”、“心有避苦求乐性义”、阿黎耶识等五种见解。这里,所谓“冥传不朽之性”,指心神不灭,既可随缘轮回生死,又可觉悟成佛。梁代光宅寺法云以“心之避苦求乐”为正因佛性,因为“一切众生,无不有避苦求乐之性,实有此避苦求乐之性”(《大乘玄论》卷三)方可厌苦而乐求涅槃。此说亦偏于“心用”而言佛性,着重强调“心”的主体功能,实际上与佛性本体大有悬格矣。梁武帝以“真神”为正因佛性,其旨首先将“心”分为“性”与“用”两方面。就“心神”之性言,以不断为精,不断故可归于常住;但性虽不断,而心之“用”则不免于流转、无常。梁武帝于是说:“夫心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兴废,一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即无明神明也。寻无名之称,非太虚之目,土石无情,岂无明之谓?故知识虑应明,体不免惑,惑虑不知,故曰无明。而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异用,无明心义不改。”(梁武帝《神明成佛义记》)心是“本”,生灭是“用”,“本”只有一个,而生灭各各不同。心之本性是明,但因烦恼污染故不免有惑,此即是“无明神明”。正如上述梁武帝所言,“神明之心”有不灭的一面与生灭的一面,不灭者即是“真神”。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言之“灵魂”。
上述两类观点,第一类将佛性归之于“众生”或“六法”,失之于具体、笼统,缺乏抽象思维之深度,用佛学术语讲,即将佛性误为生灭无常之有为法,失误彰著。第二类则力*将佛性依托于“心”。然而,或误以“心用”即功能为其正因,或误将传统之“灵魂”乔装打扮杂入佛性之中,其得在于分心为“体”、“用”两方面,失在于或太偏重于“用”,或误解了心之本体。比较而言,以“理”为正因佛性庶几近于讲清楚佛性之本体为何。
以“理”为佛性本体实际上起源于竺道生。在道生之后,又有宋代新安寺法瑶、太昌寺僧宗、梁代灵根寺慧令等人认为众生所具有的“成佛之理”是正因佛性。瑶法师说:“众生有成佛之理。此理是常,故说此众生为正因佛性”,而“此理附于众生”(隋吉藏《涅槃经游意》),众生“见虽异涂,不变佛性受身不同,佛性不改也。凡夫偏执,虽复竭思,终不能得见正理也。”(《涅槃经集解》卷十九)这就是说,此“成佛之理”乃隐藏于众生之中的不变的“正理”。众生不论见解如何,受身(种类)不同,但都有此不改的佛性,只是因为被烦恼所遮蔽,才不为自己所见,只有“闻见佛性,方生信解”(同上),才有可能见性成佛。这一道理,法瑶之徒弟僧宗论之更清楚:“性理不殊,正以隐显为异,若舍我归彼,是弃本从末,非谓真归,是以劝令深识自身当果之性”(《涅槃经集解》卷十九);又“性理是常,众生以惑覆故,不得常用。虽未得常用,要是常因。”(《涅槃经集解》卷五十四)据此,佛性与理是等同的,显时为性,隐时为理。佛性之理,超出于万物生死之外,但又为众生所秉持。所秉之理即为佛性,虽被烦恼覆盖而不显,但它却是众生达到觉悟的常恒依据。
梁代宝亮法师以“真如”为正因佛性。他以为“真俗共成众生,真如性理为正因体。何者?不有心而已,有心则有真如性上生故。平正真如,正因为体。”(《四论玄义》卷七)宝亮以为,众生之心乃依于真如性而生。佛性之体,妙质恒而不动,其心用则常改而不亡失,前者为“真”,后者为“俗”,然而“真俗两体本同,用不相乖,而暗去俗尽,伪谢真彰,朗然洞照,故称为佛。”(《涅槃经集解》卷一)众生之“真体”被俗用所遮蔽,一旦除尽这种遮蔽,真体便焕然朗现,众生便可成佛。无情与有情相较,二者同具真如之体,但无情无有心识,因而没有佛性。唯有有情既具有真体又有俗用,所以才有佛性。因此,谈论佛性须“真俗共成”方可区分有情与无情。
如果说围绕着正因佛性发生的讨论,主要由于对佛性本体之深浅不同、角度不一的理解所致,那么,佛性“本有”抑或“始有”则是围绕着“本体”与“修为”、“因”与“果”而展开的。“本有说”主张佛体理极,性自天然,一切众生本自觉悟,不假造作,终必作佛;始有说”则认为清净佛果,从妙因生,众生觉悟,待缘始起,破障开悟,未来作佛。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纯宗教的关于佛性之释名定义问题,如,是以“因”释佛性,还是以“果”释佛性,是以“行”释佛性,还是以“理”释佛性等;有佛性学说中的哲学问题,如原因与结果的相互关系问题等等。
佛性“本有”,还是“始有”?诸大乘经本来就说法不一,甚至一部经典中亦有不同说法。中土僧人各据一典,或同取一典,所取不同,因而各持本有、始有之说,立论各殊。主本有者以“理性”和“因性”释佛性。既然真理自然,佛性常住,因而说众生本有佛性。主始有者以“当果”说佛性,望“果”说始有。佛果从妙因生,众生本来杂染不净,自非妙因,因而众生之于佛性,自然为始有。然而,众生既有佛性,必得佛果,但于凡位原未得果,望众生将来得果,说佛性始有。另外,此始有义除上述二义外,尚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认为阐提现在虽无佛性,未来当有。
从理论内涵言之,本有说强调众生先天或先验地具有佛性,故返本还源即可成佛;始有说强调众生当来必得成佛,因而以果推因,众生便逻辑地具有佛性。既然是逻辑地“具”而非现实地“具”,因此修道成“性”尤为重要。从南北朝时期看,本有说、始有说的提倡者都强调修道,然而却并不能完全磨平二者对修道之重要性的认识分歧。这一歧义此后于隋唐诸宗之中仍然隐然可见。
由涅槃师引发,成实师、地论师争相涉足的“当常”与“现常”,即佛性始有抑本有之争论,纷纭数百年,难得正解。其实,二者源于佛性的释义不同而结论不一,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本有与始有二说,一是以作佛之性,从成佛的可能性去说佛性;一是以佛之体性,从成佛的现实性去释佛性。说各偏一方,对宗教修持有碍,因而后来有各种调和之论,如“亦本亦始”、“非本非始”、“本始相即”等等。此处从略。
在竺道生之后,随着《大涅槃经》的风行,涅槃学迅速取代般若学的地位而成为佛学的中心议题,中国佛教内部也由此热衷于心性问题的探讨。这不仅对于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且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心性”转向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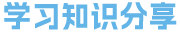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