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白居易轶事:糊涂老者
轶事,汉语词语,意思是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事迹。下面是为大家收集的解读白居易轶事:糊涂老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解读白居易轶事:糊涂老者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上《百家讲坛》演绎中唐诗人白居易,第一讲就提到其谒顾况的故事。现将陕西省渭南市志办公室姜子扬先生发表于《陕西史志》(2001年第1 期)《白居易谒顾况事的传闻与考订》摘录如下。
最早是唐末张固的《幽闲鼓吹》载:“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此后,《旧唐书·传》《新唐书·白居易传,》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宋朝王谠《唐语林》卷三,元朝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等均载此事。但对该事的时间和地点说法各异。
《幽闲鼓吹》:白居易“应举初至京”;
《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年十五六时”,未说地点;
《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未冠”时,未说地点;
《唐才子传》:白居易“弱冠未达,观光上国”;
《白居易年谱简编》:白居易十八岁。在长安;(顾学颉编)
吴言生编著《文坛风流录》:“唐德宗贞元四年(788),16岁的白居易来到京城洛阳”。
关于《幽闲鼓吹》和《唐才子传》系指白居易到京城长安应试,当在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28岁。但此前十年,顾况已被贬饶州任司户参军,不在长安。《中国文坛掌故事典》就此事说:“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云:顾况在长安任秘书省在贞元三年至五年三·四月。据此,后人多以为白谒顾事不实。”但,按语接着说:“又,白《得湖州崔十八使君喜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诗末自注:‘贞元,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而白登科实在贞元十五年,贞元凡二十一年,十五年未可谓“初”;疑居易误把初举之年当作登科之年。则《幽闲鼓吹》等所述,仍可能是事实。”这段话的意思是,贞元初白居易到长安应进士试,有可能见到顾况。但这只是顾况的行踪,而非白居易行踪。据专家李中编《白居易在渭南故里》等书载,贞元初,白居易随父避战乱,流落江南苏杭一带,不可能在长安。
1956年,万曼著的《白居易传》中说:“白居易以所业谒顾况事,见《唐摭言》等书,都说白居易当时十五六。可是在788年(贞元四年)以前白居易到长安是不可能的。贞元五年以后,顾况就因为嘲谑贬官饶州。”
近年,对于白居易谒见顾况的地点,摒弃了“长安”说,采取了衢州或苏州。如1998年大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白居易》的《附录一白居易生平创作年表》中记:贞元五年(789)十八岁。在衢州。顾况贬官饶州,路经衢州,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诗谒见。又2000年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吴伟斌著《白居易全传》中说:白居易十五六岁时,随堂叔白季康职务的变迁,白居易跟随堂叔来到苏州,当时诗人顾况贬谪饶州司户,正在苏州刺史韦应物处做客停留。在叔父的指引下,白居易单独来到顾况暂住的街坊。
大连出版社和长春出版社的说法,接近贴合白居易与顾况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的行动轨迹。对白居易谒见顾况的佳话,有了较大的可信度。
此佳话的疑云产生在唐朝张固的“应举初至京”几个字,把白居易谒见顾况的时间,地点弄错了。张固《幽闲鼓吹》成书在唐末,千百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传颂这段佳话的同时,又带着问号和遗憾,来探索。
为此,姜子扬先生认为,凡写历史人物,必须在时间,地点上要认真,以免让后人质疑。
笔者又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白居易年谱》第十二页:贞元三年丁卯(787)十六岁,其中述及“贞元四年(788)以前,居易无赴长安之可能,贞元五年后,顾况即因嘲谑贬官饶州司户,复至苏州,与苏州刺史韦应物,信州刺史刘太真相往还,如谓居易有谒顾况之事,或相遇饶州及苏州也。”
拓展阅读
诗人介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文学成就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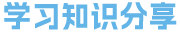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