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散文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都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散文吧?散文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取材广泛,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你知道写散文要注意哪些问题吗?以下是精心整理的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散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变老之际,我总是莫名其妙觉得,那个有着黄土夯筑、水泥抹面的偌大锅台的屋子才是我梦中的家;那个山坡上埋着先人骨殖、田埂小路往返的牛羊农人身影的村庄才是我真正的故乡。
行走在光阴里,行走在一生纵横交错的道路上,我一直在思索关于村庄的定义和蕴含。最早,我以为所谓村庄,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个树木掩映、土地广袤的所在。那里,有顺着土屋墙根蔓延到村口、又爬上乡间小路后扩散到远方的青青野草;那里,有高出屋顶随风飘荡的缕缕淡蓝炊烟;那里,有如细绳般伸缩开来而又收束回去的、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
拂过树梢掠过草叶的风,吹走了我的少年时代,抹平了我身上乡间生活劳作的印记,但却把我有关童年、有关村庄的记忆,撩拨得愈发的清晰和逼真,就像轻抚水面后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层,由远及近,恍惚到清醒,在我的心头和思绪中一波波来袭。每当我心烦意乱,竟让我坐卧不安无所适存,突然想到庄稼地里去转转,到乡间小路去走走,明净一下心思,顺畅一下呼吸。
我知道,我所经过的那些很多村庄是别人的村庄,只会出现在其他游子的梦境。别人的故乡小路上,没有我的足迹,没有我童年的身影,没有我所熟悉的味道。而每个人记忆深处的故乡,都是一个与众不同而又无法替代的存在,都是一个让其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念想。
那些以村庄为圆心,辐射开来又聚拢进去的乡间小路,曲曲折折纵横交叠。总有那么一两条,一头牵着你的村庄,一头拴着渐行渐远的你,仿佛与生俱来永远无法割弃的脐带,联接着你的根,束缚着你的魂,给你希望,给你营养和动力。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的步履铿锵亦或磕磕绊绊,都会若即若离拉扯着你。使你在跋山涉水的间歇里不由自主的转身伫望,使你在日暮途穷的疲惫中想回来酣畅恣意的憩息。
我的村庄,坐落在一片山势和缓的黄土坡洼中。村庄辐射东南西北小道、上下纵横的路,一端通向前往县城的马路,铺着砂石,宽阔而平坦,有大小汽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走;一端顺山势向下迂回,直抵两山夹缝处的清浅小溪,被牛羊的脚蹄与祖先的汗水、踩踏浇筑的坚硬瓷实,散发着牲畜身上的淡淡腥臊与呛人的黄土气息以及路旁艾蒿与白杨树叶子被太阳晒软后、蒸腾出来的既温润清新又干燥苦涩的味道,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苍白的光斑,映衬得路旁的野草黑绿发亮避人眼目。那些左右纵横的小路,通向山野和土地,种植我们的庄稼,埋葬我们先人的棺木和身躯。时常有山坳间的硬风,卷裹着脚下的黄尘隆隆赶过,风声里似乎夹杂着黄牛耕作时粗重的喘息,甚至还伴随着先人悠长的呼唤与悲怆的叹息……在好多个夜晚,我一直梦见,喧嚣了一天的故乡在异常沉寂与凝重的夜色里,农人酣睡,牛羊已入梦乡,粮食生长、成熟的浓郁气味水一样弥漫,唤醒了地下先人的幽灵,他们扛一把撅头,握一把铁锨,步履缓缓行走在寂无人声的乡间小路上,查看着庄稼的长势,这里挖挖,那边掏掏,埋怨着好逸恶劳的后辈,前言不搭后语的嘟嘟囔囔诉说着村庄旧事和他们的艰辛……
幼年的我,双腿纤细,步履踉跄,在山坡上放牛,一眼就瞥见山对面我那黄土包裹中绿色招摇的村庄,还有细瘦如丝的田间小道。觉得我的村庄是一只面目狰狞的八脚蜘蛛,那些小路是他不舍昼夜、用心险恶编制出来的丝茧,笼罩了我的梦想,遮蔽了我的视线,牵绊着我的脚步,使我走不到那一座座大山的尽头,使我看不到那遥远的未知……
那时候,我总以为,不停走,走完乡间小路,越过远山阻隔,直至走到天地相接的地方,就会到达一个未知的神秘所在,而那里天高地迥,日新月异;那里花红柳绿,云淡风轻;那里,天上飞飞机,海里跑轮船,地上条条大道也宽阔笔直,能通往象征着成功的罗马,能通向尼瓜拉加气吞山河的大瀑布……
我的童年,有一段时间,我自以为是屈辱的.,源自于我小时候无休无止的放牛生活。我家的五头牛就像村子里狡猾善变的无赖。拴在圈里,眼神温和神态安详,一副谦卑老好人的样子,可是一旦解开缰绳走了家门,在村口一圈大柳树围拢起来的大涝池中伸长脖子喝足水后,五头牛就不约而同开始暴露出一种刁钻狡诈的流氓本性。它们撒开四蹄,在两边绿色庄稼遮掩的小路上风驰电掣般狂奔,迅速伸长脖子用舌头飞快的卷起一把麦苗、撕扯掉三两株玉米,边跑边吃,边嚼边跑,在乡间小道上腾起一股白尘。跟在牛后面的我,挥舞着鞭杆,追得满头大汗,喉咙冒烟,胸腔像风箱一样剧烈动荡。每头牛都有四条粗壮的腿,我只有两条,而且那么纤细无力,注定追不上这群蠢物。我跑得快了,牛就跑的更快;我放慢了步伐,牛就立刻慢下来,瞅准空子,又抢掠了几颗谷穗和一株玉米,一半嚼在嘴里,一半拖在蹄下,然后又开始狂奔。
那时候,我一直痛恨、埋怨村子通往山里的乡间小路太长,在追牛的奔跑过程中,那蜿蜒曲折的小路好像一直没有尽头,没有了断。小路两边的庄稼一片又一片的浅黄深绿,齐刷刷的擦着我的耳际和鬓角,断断续续的跑到了我的身后。在地里干活的人看到我家的牛抢吃了自己地里的庄稼,就用不干不净的话,大声吼喊,开始叫骂我家的牛,也喊骂着一路小跑跟在牛屁股后的我。我一边追着牛跑,一边抹着眼泪,心里既憋屈又气愤,用骂人的脏话,也胡乱的叫骂着不服管教惹是生非的牛。那种境况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是多么的渴望长大、渴望增添力气啊!我想,等我长大腰粗腿壮之时,我必须把自家的牛驯服得规规矩矩,像狗一样服从谄媚主人,能看主人眼色行事;我还想着,等我长大有出息后,要把今天大人骂我的脏话,一点不落的回敬给他们,双手叉腰,唾沫星子喷他们一脸……
牛终于被赶到了山里,我可以松一口气了,我抱着鞭杆守在山顶通往庄稼地的路口。我家的五头黄牛散漫随意的在缓缓山坡上吃草,吃得不紧不慢,吃得执着和认真,吃得那么虔诚与专注,简直就像热爱学习的小学生在一丝不苟的温习功课。我坐在厚厚的茅草丛中,看山腰上一棵被方向不定的风把躯干刮得七扭八歪的矮身子杜梨子树;看夕阳一寸一寸染红对面的山崖:看夕阳中一簇山丹丹渐渐变成一种梦幻般的蓝紫色;看对面岩石罅隙中噗噜噜飞出的一群白鸽子,慢慢升上天空,然后消失在洁白低垂的云朵后面。
山的对面,就是我的村庄,它纵横交错在绿色的黄土小路,更像一只蜘蛛经纬分明的网,走在路上稀疏的人是一个黑点,像蚂蚁一样小。天幕已经低垂,鸟儿已归巢,搁在西山山尖上的太阳只剩一个圆圆的红圈,就像有人拿胭脂均匀涂抹的一个井口。我放牧的五头牛肚子滚圆,牛角上挂着我挖来的柴胡,步履悠悠眼神温顺,和我结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起走回我的村庄。没有午间的炎热,乡间小路两旁的庄稼郁郁葱葱,像屏障一样簇拥着我和牛。微风拂过,带来庄稼再生长过程中挥发的氤氲水汽,漫过我的衣襟袖口,漫过我的眉梢心底,让人想浅唱一支舒缓的歌谣,想低吟一首绮丽的小诗。
此刻,在夕阳落山的黄昏时分,我——一个在很多条路上踽踽独行、并且跌过跟头乃至弄得鼻青脸肿的中年男人,独坐窗边静思遥望时,仿佛故乡的一块地头上、一蓬草丛中,半截土墙边,有一种叫着我小名、既遥远有真切的声音在呼唤着我,让我在心浮气躁、力倦神疲之际,想迫不及待的走回我的村庄,在长着庄稼、蔓生着野草的乡间小道上,走走停停,掐一把葱叶嚼嚼,掘几枚草根闻闻,任晚风拂乱我的衣襟和头发,抬头望天,低头思考,让一些散漫的思绪同天上的流云一起,悠悠舒展和漂浮……这里是一块麦田,像铺就了一片厚实的绿色大毯。丛丛麦苗都那么茁壮蓬勃、严严实实,无孔不入的风儿都找不到刺钻进去的缝隙。右边是一畦金黄的油菜,有着向日葵的明媚笑脸和阳光般的金黄色泽,得了偏粪肥的那几株就像羊群中的骆驼惹眼和倨傲,俯视着其他低它一头、你追我赶闹闹嚷嚷竞相生长的细碎金黄花朵。用铁锨拍打瓷实的一架子车粪土,被黄牛拉拽的乡间低洼不平的小路上,从两旁洒出的少许粪土造就了车辙两旁的小草,年年岁岁长得旺势,鹅黄的肥硕鲜嫩,深绿的坚挺发黑。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田野中弯腰劳作的父老,身形佝偻,皱纹间积蓄着黄尘,脸庞上刻满了沧桑。他们小心翼翼接过我递给他的香烟,郑重的别在耳朵后面,和我高喉咙大嗓门谈论着今年庄稼的涨势、近期天气的变化以及农药化肥蔬菜种子的价格跌涨。小时候牛吃庄稼时他们对我恶毒的咒骂,还有我对他们咬牙切齿的恨意,全部烟消云散,好像从来就没有在我心头滋生和停留过。
信步走着,乡间的小路牵着我的步伐,就像当年我牵着牛驴的缰绳一样。一看到路旁葳蕤的野草,我就不由自主想拿起一把锋利的镰刀,连跪带爬把它们全部割倒,一码一码堆放整齐,填塞进我的背篓,切碎铡细后,倒进牛槽,把我家的五头牛喂得脊梁浑圆皮毛光滑,连苍蝇拄着拐杖都无法立脚。可是,在难以挽留和捕捉的光阴里,我家的五头牛拼尽了一生的力气后,现在走向了哪里呢?我的镰刀又丢在哪里了呢?我那甜蜜而忧伤的童年又去哪儿了……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双腿如椽迎着朝阳站立,看着路旁丛生的野草和灼灼小花,摸着几近不毛的脑门,我怅然若失的发现,那些很多童年熟识的野草与野菜,到底还有几种我不能假思索的叫得出它们的名字?那个刺如皂荚开着白花的荆棘叫狼牙刺吧?那个掩映在麦田中抱着臃肿肚子的细瘦身材植物叫王不留吧?……我只能依稀分辨,那个我当年割胡麻不小心划破脚腕后、母亲拧出汁水止血消肿的小草叫刺芥;那个如向日葵般顶着金黄小圆盘的能卖钱的草药叫蒲公英;还有那种母亲在劳作之余,给我和妹妹编制出小松鼠小兔子的毛茸茸小草是狗尾巴草吧……那个叫辣辣的小草,到处都是,长在场圃里与门前的小路上,叶片细碎,一大团一大团聚拢成一片,就像人类分散又群居的部落和村庄,互不干涉又遥相呼应。小时候,我们爱咀嚼它的叶子和根茎,觉得辣味过后是一种清凉芬芳的口感。可是,当我拔起一颗放在嘴里吞咽时,却只有苦涩和泥土的腥味,完全没有了童年时那股从喉咙径直奔泻到口腔的涎水和吸引力。我才知道,我的童年,我记忆中野草的滋味,还有村庄里的许多老人与旧事,竟和我长大后的行进方向背道而驰,愈行愈远,连一个纤细的尾巴都难以抓缚和遮挽。
那一年的某个夏日,祖母去姑姑家暂住,我顺着那一条最熟悉不过的小道去找祖母。祖母有三个女儿,这个姑姑离我们最近。我们两个村隔犁沟种地,有时候,当我们把牛吆到地头时,姑父已于晨光熹微中犁开了一圈地,像拇指的掌纹,甜腥的泥土气息,在早晨湿润的空气中扩散。到了中午,姑姑和母亲提着瓦罐出现在地头。于是,黄牛嘴里吐着白沫子站在新犁开的土地上反刍休憩,人从地边的杨树上撅下两根树枝当筷子,蹲在地头吃午饭。新翻的土壤上,缕缕白气在日光下漂浮,人的咀嚼吞食声响成了一片……
那一天,头顶的太阳火辣辣,我拿着一截柳枝边走边扑打着路旁的崁塄。时值夏日,太阳骄奢,万物噤声。走在两旁庄稼的阴影里,玉米阔大的叶片上脉络清晰,滋生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凉意。没有风,路边的树站的笔直,草木温润清香的气息直扑我的鼻孔。在已经看到姑姑村庄的轮廓、望见股股炊烟直直钻进天空的时候,突然从右面的玉米地里扑出来了一条大黑狗。它急促的喘息着,粗壮的腰身一收一放,吐露着红红的长舌头,双眼炯炯白牙森森,挡住了我的去路。那条狗在我的记忆中,像一头小牛犊那般壮实。它开始吼声如雷的驱赶我,把我当成了一个偷盗粮食的小贼。终于,它毫不费力的撵上了我,在我羸弱的屁股上轻轻用尖嘴冲撞了一下。我倒在地上,屁股朝天,胸腹紧贴大地,开始没命的扯开嗓子大哭。也许是我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了那条黑狗吧,也许是那条黑狗没料到它的敌人竟如此不堪一击吧,它在我的头发和脸颊上草草嗅了嗅后,就大摇大摆旁若无人的匆匆钻进了那一片深黑的玉米林,好像一股风刮过去后不知来路更不辨去向,与庄稼草木融为一体。那条黑狗的利齿,并没有伤及到我的皮肉。可是,到了姑姑家后,我却一下子萎靡不振。整日的坐在门槛上,呆呆的看崖畔漂浮的云,看公鸡咕咕咯咯领着一群毛色斑斓的母鸡在草丛里觅食,看墙壁上纵横交织的裂缝。晚饭只匆匆扒拉两口,晚上睡觉会突然从梦中惊醒,双股颤颤满头冷汗。而尿床的旧病,也开始无法避免的重犯了。
第二天晚饭后,头发花白的祖母和系着红色方格头巾的姑姑,一老一少牵着我的衣襟,在我遭遇黑狗的乡间小路上,在夜色如泼墨时分,一前一后,声音一高一低,给我叫魂:“狗蛋,回来吧……狗蛋,回来吧”。然后,在提前叮嘱了我的那一声有气无力的“狗蛋回来了”的应和中,我的两只衣兜里装着我跌倒现场的一把干土,回到了姑姑家,一夜睡得安稳。第三天,东方一泛白,就和我的表姐表哥,赶着一群羊,在山间趟露水,摘青杏,挖药材。
多年以后,再次经过那条小路,我总下意识觉得在阳光炎热的晌午,会有一条黑狗蓦然从玉米的阴影里扑出来。只不过,肯定不是当初那条狗。有时候,我竟然还会产生这样一些痴傻的想法:那一天,也许对那条狗来说是个平淡的一天,早就从狗的记忆中抹去了,但对人来说,却永远忘记不了,直至多年后,我还能想起它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时的神态与样子。我还想,当年那条袭击过我的黑狗,现在还在人世吗?如果在,又老成了什么样子呢?狗的一生,到底有过怎样的阅历和见识呢?它若再次和我重逢,它的狗思维里有没有保留着那天恐吓一个小孩的清晰记忆?它能认出长大成人的我吗?面对现在牛高马大的我,它会不会恐惧与悔意顿生,惭愧的低下它的狗头?……那一晚,乡间小路上,我的魂,由于一条黑狗突如其来的骚扰,被吓得蛰伏在路旁的草丛中,但最终还是被叫了回来,安妥的镶嵌进我的躯体,顺溜的支撑着我长大。可是,在我以后的人生轨迹中,时不时袭来一些磨难、遭受一些打击,就像玉米地里突然窜出一只恶犬,当我心灰意冷简直一蹶不振之际,我坚定地认为,故乡——我的村庄能带给我力量,能让我恢复元气。因为那里的一处山坡,埋着我祖先的尸骨,埋着我的根;因为那里的一间土屋门槛下面,埋着我的胞衣,埋着我的魂。
故乡的小路,承载着我太多的记忆。它细瘦如绳,抛洒在原野上,缭绕在山峁间,看似千头万绪,杂乱无章,而只有我能理清它的脉络,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小路上的每一抔土丘,每一处洼地,每一蓬杂草,每一棵大树,就好像给故乡小路这条长绳打下了不计其数密密麻麻的结,但我自能分辨清楚了然于心,并且可以追本求源引发很多回忆,讲出许多旧事。那一天,村里咬文爵字的老先生楚三户,手里握着放羊的鞕杆,在一个干冷的早晨,气势汹汹和我们上学的孩子走在一起,踏着被积雪和枯叶覆盖的乡间小路,要去找我们的老师理论、讨个说法。原因是,老师们把他费尽心思给儿子起的一个响当当文绉绉、并寄寓着着自己无限期望的名字“楚中天”,由于儿子竖行拼写时分得太开,老师发试卷时误读成了“林蛋大“。由此导致他儿子楚中天,被村里的小孩,庄里的大人乃至村小的老师,都一贯的直呼起外号“林蛋大”,以致忘了他的大名楚中天……
楚中天在上小学时,一直被我们亲切地称为林蛋大同学,直至他连续留级后十七岁小学毕业。楚三户老先生一心想把自己的儿子教育、锻造成一个识文断字的先生,可是事与愿违。许多个冬季干冷的早晨里,路旁的树木披霜挂银,楚三户嘴里呼着白气在积雪中拉扯着架子车,架子车厢中盛放着被老子强行捆绑手脚、打死也不愿进学堂念书的儿子楚中天去上学,这成为乡间小道上早晨朝阳初升时一个不伦不类的风景。五年级又留了两级后,楚中天就被学校以年龄偏大为由,发了一纸毕业证劝其退学了。于是,村庄里识文断字的楚三户老先生,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的放弃了对儿子的培育,把羡艳的目光转向那时学习很好并且考上了中专的我。上学期间,寒暑假回家,他就急忙来到我家破烂不堪的窑洞中打招呼,郑重其事的和我握手,跟我讲一些我也费解的之乎者也,并称呼我为小友。
数年过去,当初被老师当做反面教材来教育其他学生、并一直称呼其为林蛋大的楚中天,个头猛蹿,由于早早出去打工,竟在故乡以外的土地上混得脑满肠肥,成立了公司。在市里买了房子后,把爹爹楚中天一生积攒的家当,丢的丢送人的送人,开了一辆路虎,把穿着一身熨烫得平平展展的深蓝中山服的楚三户,接到市里的高楼去享清福颐养天年了。那一天,村里的乡亲都来送别,看着楚三户在车里挥手远去,乡亲们都说,楚老先生这一去,村子里过年时,将无人义务写对联了……他老人家的字,写的真黑,真好。以后再也出不了这样有文墨有学问的先生了……再次见到他,怕该是他驾鹤西去埋归乡梓的那一天了吧……
在人们的叹息余音还未被乡间小路吸纳、扩散至了无痕迹时,间隔不到半个月,楚三户却又突然出现在村巷中,依旧穿着那一身熨烫平平展展的深蓝中山服,仍然肩上扛着铁锨,铁锨把上挑着粪笼,每天东方刚呈现出鱼鳞白之际,便一个人踽踽独行在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上,走走停停,这里剜剜,那里掏掏,堵塞一个田鼠窝,拍平一处车辙印。
楚三户说,城里的高楼要用一个直上直下的铁匣子才能运送到家,屋里没有锅头,待在其中不由得心慌气短,就像借住在别人家里;公园里的花木,修剪得齐齐整整但没有丝毫精气神;城里的人群熙熙攘攘你拥我挤,找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听不到一句亲切的家乡话,每天忒憋屈;城里的狗穿着衣裳,人却露着白花花的肉,怪模怪样看着闹心;在城里的炕上睡觉,就像飘在云端,软绵绵荡悠悠没有一点踏实感……还是村子里的老屋和田间的小路联接着地气,走一遍心明眼亮,望一望气顺心宽。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戴着眼镜的双眼,远没有脑袋上扣着瓜皮小帽的楚三户老先生那么敏锐,他会早早认出我。于是在老远,就立住铁锨放下粪笼,用乡下人还不太习惯的仪式,拂拂衣襟,掸掸袖筒,伸出双手和我来握。我捏住他的手,觉得干燥而有温热,就像太阳照耀下经年的土皮,就像刺破岩层深入土壤的树根。而后,我们说着话,并排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像那遥远的先人在行走一样,就像那未卜的后代再顺着我们踩踏而过的脚印在前进一样,还更像两株行进中的植物走在地头阡陌中,长在路边嵌塄上,我们的根,深埋在村庄的纹理中,纠葛在村庄小道两旁野草的枯枝败叶里、以及庄稼新生的根须和枝桠间……
转载请注明出处记得学习 »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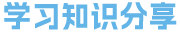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