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下面是收集整理的试论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希望大家喜欢。
史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独具美学特质的唐诗始肇时期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的诗群;其诗作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座丰碑。无论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还是诗体的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唐诗发展风貌。本文将对初唐四杰诗歌的题材内容、诗体的形式和诗歌艺术风格进行分析,以明确四杰在唐诗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更好地把握初唐诗歌极其整个诗歌的发展历程。
一、特定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是远离经济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任何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都离不开那个特定的时代。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无一例外是初唐诗坛那一特殊时期的重要诗群。他们大都生活在唐太宗贞观中期以后至武则天期间,大唐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唐太宗所创造的贞观之治,不仅在物质文化上创造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在历经数百年的战争***、动荡压抑之后,在精神层面上对整个社会的鼓动具有更大的鼓舞力量,这对四杰一类的士人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个个摩拳擦掌,渴望有所作为。初唐统治者还总结吸取了隋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门阀制度的崩溃。科举制度逐渐推行,到武后当权后通过科举或直接从没有背景的士人中拔选、录用官员制度的形成,这对士人的心理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仕途充满自信。然而,在初唐这只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上很快取得了进展,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而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却不能迅速跟上初唐政治经济的发展,仍承袭浮艳绮靡的诗风。不但虞世南、李百药等陈隋旧臣继续在写宫体诗,就连“一代英主”唐太宗也喜欢宫体诗,写的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如《采芙蓉》中就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而当时,替唐太宗修改文稿、为唐太宗所宠信的上官仪,也是秉承陈隋的遗风,更是以写“绮错婉媚”的宫体诗见长。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诗人称他的诗为“上官体”。他的代表作《八咏应制》,津津乐道于浮华侈靡的宫廷生活,除了金玉珠翠的堆砌外,还暗示***,格调极低。他还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对”、“八对”,这虽对后来律诗的形成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绮错婉媚的风格和“六对”、“八对”的形式,对当时诗歌的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和束缚、限制的作用,造成了“诗以极衰”的局面。
然而,物极必反,衰颓到了极点,转机也来了。魏征、王绩的作品,开始透露了初唐诗风轻变的音讯。魏征的《述怀》,抒发了他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抱负。那种 “执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英雄气概,一扫唐初的柔靡格调。王绩的诗多数写田园生活的闲恬情趣,平淡自然,跟专事雕饰、华靡的时风完全不同。他那首著名的《野望》写他的隐居生活,开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王绩以他描写田园景色和闲适生活的诗篇,突破了初唐诗歌以描写宫廷诗为中心的狭窄范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进一步开拓诗歌的题材,转变诗歌的风格、发展诗歌的形式,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救出来的是“初唐四杰”。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四杰》中对四杰概括的十分明确:“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杰的出身、经历、生活道路也不同于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虽多出身士族,祖上也曾有过显赫的时候,但随着整个社会门阀制度的衰落,到他们祖父、父亲一辈相继转入消沉,故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基础,实际上他们已属庶族地主阶级。正因为他们这些特定的出身背景以及与社会的磨擦养成他们与世不融的性格。他们有着他们这一阶层所特有的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他们饱读诗书、才华出众,有着强烈的仕进愿望,渴望建功立业。可是,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坦途,仕途蹭蹬,这样更加强化了其行为的反常性,与整个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感,对上流社会更具有一股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们的诗歌观念、诗歌活动形式自然与流行的雕章琢句相左,他们反对游戏之文,要求抒发人生意气。
二、“四杰”的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
(一)题材的拓展
诚然,贞观君臣学士最早对南朝诗歌进行纠偏改良,倡导中和雅正的文学,一改六朝浮艳轻靡的文风,使诗创作走向清丽典雅的道路。可惜上层贵族的创作多以奉和应制与歌功颂德、游宴唱酬而愉悦性情为总归,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一次宫廷文学的内部调整,其意义在于为唐诗的开创清扫了道路。①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崛起于诗坛,才真正为唐诗的创建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力*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局面。四杰诗和那些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不同的地方,即是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也较为接近人民。尽管他们也无法避免封建文人的命运,不能不匍匐在帝王的膝下,但不同于一般的宫廷文人,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福利和享受,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也不是以文事人,仰人鼻息,而有着***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着他们诗歌内容的特殊状态。明代陆时雍《诗境总论》评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锦色。”所谓“六朝锦色”,是指他们的诗仍有六朝宫廷诗的斑斓色泽,但是宫廷诗风毕竟不是他们诗歌的主导倾向,他们文化生活的价值在于承袭基础上的革新:“正如宫诗体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道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汉。”②四杰都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在仕途上,他们都坎坷不遇,背景离乡,辞亲远游,过州历府,聚集京都,结交天下豪俊,渴求达官显贵,进而科举应试,为人府属,外出做官,甚至从军边塞。梁实秋有云:“年小而名高,命运多坎坷。”而正因为这样,使他们接触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激发起广泛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促使他们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隘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内容,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四杰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是齐梁诗的继承者,但比起齐梁到陈的浮艳的诗来,四杰的抒情诗(包括咏怀、咏史、送别的诗)内容是大大的丰富了,写景、咏物的诗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们可以通过“四杰”的具体创作来看它们的丰富内容和艺术水平。
首先,值得一谈的是咏怀诗,它可谓是四杰诗中的一大类。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是诗人生命中的艺术活动,是诗人心灵历程的艺术呈现。“四杰”生活在李、唐王朝政权获得巩固并向极盛的顶峰发展的时代。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其“咏怀”诗中集中体现了自我的情志怀抱。四杰诗中表达自己不得重用,渴望建功立业,不甘碌碌一生的理想作品不在少数。卢照邻把自己比作“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穷鱼赋》)的东海巨鳞,很容易联想到李白笔下的大鹏,又如他“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无由召宣室,何以答吾君”(《至望喜瞻言怀贻见外知己》),以及“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餐白玉兮饮琼芳,心里荃兮路阳长”(《中和乐九章》总歌第九),无不体现内心的苦闷和不得志的忧怨忧而又显梗慨而多气的情怀:杨炯在《出塞》、《紫骝马》、《从军行》中一再表示:“丈夫皆有志,会是立功勋。”(《出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紫骝马》):“宁为百丈夫,胜做一书生。”(《从军行》),这些豪壮的诗句,洋溢着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这在唐以前的同类诗中是找不到的。隋代杨素的《出塞》、卢思道的《从军行》是当时的有名之作,前者写出了塞外的荒寒的景色,有一定的真实情感,后者描写了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哀怨佳丽,但是调子都较低沉,其它作品就不用说了。而四杰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用热烈、豪放的笔调来写,表现了唐代人民一度不以征战为苦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王勃把自己描绘成“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华饰。”的莲花。他坚信,“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香藻凤池。“(《金莲赋》)。卢照邻还在《咏史》四首中歌颂了汉朝的季布、朱云、郭泰、郑太四位著名人物。他称赞季布道:
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
处身孤目直,遭时坦而平。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
他借季布的“孤且直”来嘲笑封建社会里的那些“唯唯”的群公,对于季布的“髡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而由于“汉祖广招纳,一朝拜公卿”的身世十分羡慕,羡慕他“处身孤目直,遭时坦而平”,表示“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同样,他赞颂了“愿得斩马剑,先斩佞臣头”的朱云,“诸侯不得友,天下不得臣”的郭泰,这些诗与左思的咏史诗相似,借历史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较言之卢诗更显得激昂。胡震亨有云:“诗人咏史很难,妙在不憎一语,而情感自深。”(《唐音葵签》)。我们再将骆宾王的《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叙寄员半千》、《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咏怀》等咏怀诗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诗人是淋漓尽致的书写了人生情怀为主题的,渴望为时所用的热情与长期坎坷失望的牢骚,投笔从戎博取军工的幻想与辗转边庭不得升迁的苦恨,豪侠放浪的性格与久遭幽挚的愤懑,错综交织,构成了诗人深沉的咏叹调。他把自己比拟成稀世的宝剑:“讵怜冲斗气,犹向匣中鸣”(《和李明府》),表示:“君恩如果报,龙剑有雌雄。”(《边城落日》)。在《狱中书情通简知己》一诗中,他认为自己虽然暂时是东汉赵壹那样不得志的“汉阳穷鸟客”,但终究会成为大展经纶的“梁甫卧龙材”——诸葛亮!在《畴昔篇》中他自述了身世的悲凉,说是“垂钓甘成白首翁,负薪何处逢知己”。他还写过一首(《浮槎》序),他这样悲伤的吟道:
似舟飘不定,如梗泛何从?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
陡怀万乘器,谁为一仙客?
他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也说过:“穷经不沾用,弹铗欲谁中,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这些都为个人的各位打算,应予以批评,但从中也多少看到贤才不得重用的封建社会的政治情况。在当时那个社会里,他也只有大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在狱咏蝉》)“生死交情异,殷忧岁序阑,空余朝夕鸟,相伴夜嘀寒。”(《宪台出絷寒夜有怀》)。在这些滚烫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完美的自我形象,刚直清醒的进步志士的社会的黑暗腐恶势力的悲剧性冲突,以及和蓬勃向上的时代同步搏动的脉搏。因此,他们幻想着有朝一日“会当一举风尘,翠盖朱轩凌上春。朝升玉署调天纪,夕憩金闺奉帝纶”,坚信“长卿未达终希达,曲逆长贫岂剩贫?年年送春应未尽,一旦逢春自有人。”(王勃《春思赋》)字里行间充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和乐观精神。
诚然,较之盛唐之音,四杰这些诗所反映社会面还不够深和广,还没有把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刻画出来。但是,我们应注意到,这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开山之力,功不可没。由于他们的遭遇,通过自身的阅历,不自觉的描写了社会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抒发了自己愤慨的感情,这些感情代表了众多的较正直的人士的感情,和人民的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他们的思想态度是积极的,不是回避而是敢于去面对现实。一旦理想落空,他们也绝不会自轻自贱,而是当歌则歌,想哭就哭,写悲写愁,诉怨诉怒,出于天性,不假矫饰。
即使四杰诗中所见不深广,比起前此齐梁诗和当时“上官体”的作者来却是值得我们加以肯定的,同阮籍《咏怀诗》以隐约曲折的比兴形式倾泻寓藏在内心深处无由发泄的痛苦愤懑相比,四杰咏怀诗不仅改变了艺术表现方式,少用比兴而多直抒胸臆,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闪耀着强烈的进取精神。比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感遇》三十八首中那种沉郁苍凉的调子来,四杰诗高远的理想和报负,对自由人性的追求,浪漫主义的色彩,大开大落的笔法,与盛唐诗人代表李白非常接近,也早已透露出盛唐之音的消息。
咏怀诗如此,写景诗也是一样的。四杰的写景诗直接晋宋,把所谓山水派的诗提到了新的阶段。
①四杰都是苦命才子,他们的一生都是坎坷不平的,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因此他们的思想成分是复杂的,除了儒家的用世,还有道家的出世,佛家的寂灭,在他们的作品中,求仙之章和山水田园之什也不少。其次,山川美景,风云奇色不但为四杰提供了新鲜丰富的创作营养和表现对象,而且是他们陶写胸臆的最好工具。因而他们“抑天汉而郁挫,临江山而慷慨。”
②创作了大量的写景诗,也勾勒出了社会生活的多种场面,画面要比宫体诗开阔得多,色彩也丰富得多。一方面,四杰尽力捕捉、摹写其游历生涯中所见所感的各种景观,绚丽如“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落芯翻风去,流莺满树来。”;“蒲夏荷香满,田秋麦气清。”,“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娴静如“郊童樵唱返,津叟钓歌还。”,“钓诸青凫没,村田百鹭翔”。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各种人生感触,如辞亲别友的乡关之思,羁旅行役的劳顿困苦,投闲致散的优游、放达,惜时伤春的人生惆怅,功名难就的失意悲愤,寄寓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
如王勃的著名的《滕王阁》诗就表现了诗人的极端的惆怅:
滕王高阁临江诸,佩玉鸣莺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溥云,
朱帘暮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白流。
此诗情景交融,以昔日的佩玉鸣莺,讨今日的歌沉舞歇,从而抒发万物是人非的感情。徐进评此诗曰:“抚今追昔,抒发景不长,年华易逝,江山不改,景色依旧的感慨。写得气势奔放,格调雄健,没有其它当今之作的那种消极悲观情绪。”(《滕王阁诗选》)同时,这首诗并不是一般的抚昔时今,而是在江水长流与帝子不存的对比中,寄托了时光悠悠、人生有尽而物质不灭、宇宙永恒的思想。意境开阔,气势奔放博大。可是像他著名的《仲春郊外》、《郊外即事》、《春日还郊》等诗对于事物的歌赞,给人又是另一种感觉,使人领受到诗人对大自然的喜悦和热爱。他的《对酒春园》写道:
投簪下山阁,携酒对河梁,狭水牵长镜,高花送断香。
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自然催一醉,非但阅年光。
还有他的《深湾夜宿》、《泥溪》、《长柳》、《田家三首》等诗,写风景如山水画,可是不止于画画山水而已,而是进一步从写景中烘托出和引发出诗人对于世人的感情。
杨炯的三峡诗(《广溪峡》、,《巫峡》、《西陵峡》)既是写景,又是咏诗和抒情。这些诗展开了雄奇魂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作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水,千载伸知己。”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此外他的《和石侍御山庄》和一些入道观的诗虽然写景细致,但不如三峡诗幽美。其《早行》、《途中》两首则颇有情意和王勃的《深弯夜宿》相类。
卢照邻的《入秦川界》、《山庄休沐》、《山林休日田家》、《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锺阳驿》所写景致都是美好的。他在成都写过一首《十五夜观灯》,他描写灯光是:“溽彩遥兮地,繁光远缀天,接天疑星落,依楼似月悬。”他又有《春晚山庄率题二首》,写田园风光,“莺啼非选树,鱼系不惊纶”,这一切的美景使他感到:“年华已可乐,高兴复留人。”《唐诗归》卷一选此诗,并说:“清润可敌子安,此即其高于骆丞处”。
骆宾王的《秋日山行简梁大官》、《晚憩田家》所写景致也是清新的,他在《送吴七游蜀》诗云:“夏老兰犹茂,秋深柳尚繁,雾销山望迥,风高夜听喧。”《春晚从李长史游开道林故山》有句道:“幽寻极幽壑,春望陟春台,……落蕊翻风去,流莺满树来。”这样的写景都是美丽逼真的。
在四杰的写景诗中,山川风物,尽收笔底,完全冲破了宫体诗殿苑风光的藩篱。特别是诗人对自我理想与人生价值的强烈关注和执着追求,大大增加了感情的浓度。这对于在隐逸风气中产生并常常流露出超然世外情趣的晋宋山水诗来说,就是一种发展,一种主题的深化。其意义不但在于改变了初唐宫廷诗的体物方向,让江山景物取代了帝苑风光,而且在于融情入景,借景抒情,扫荡了穷妍极态地模山范水的写景模式,从而将写景诗引向抒情的健康轨道,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开辟了道路。但是四杰写景比诸陶谢王孟,还缺乏一种淡雅恬静的韵味,待盛唐王、孟一派的绝句诗作出来,进一步发展四杰写景诗精工明洁晓畅的艺术趋势,进一步将感情融化在景象中,诗情物景妙合无垠又兴象玲珑的唐诗境界就臻于成熟了。
四杰的送别诗亦别具一格,成就卓然。四杰在他们漫游、为官、从军的生活经历中,朋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奔走聚散也就不可避免,而一旦分手,前途莫测,种种人生阴影难免袭上心头。于是六朝以来那种“离群托诗以怨”①的赠别诗便在四杰手中放出来新的时代光彩。既是送别,抒写离别者双方的深厚感情,就构成了送别诗的基本情调和要求。六朝优秀的送别诗,正是比较成功地表现了真实的离别情绪,但如果仅就离别情绪本身而吟咏,则很难在意境上翻新。四杰突破前人的地方就在于:写离别不作辛酸语,变凄怆为豪放,完全摆脱了过去送别诗中缠绵的儿女之情,从双方惜别的感情扩大到各自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将进步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以身世遭遇的感慨融入惜别的感情中,从而增加了送别诗的感情容量,刷新了送别诗的艺术境界。此类诗以王勃写得最好。在其《送杜少府任之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厥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令人感伤,但它非一般表现哀愁悲伤的送别诗不同,全诗笔力矫健,格调高昂,意气风发,在惜别情中容入了激昂慷慨的英雄气概和奋发进取的乐观精神,体现了奋发有为的时代脉搏,异响惊人,已是典型的盛唐之音。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云:“丈夫志在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兮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疚,无乃儿女仁!”王勃在这里浓缩成四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姚鼐评曰:“(海内寸知己,天涯若比邻,用陈思王《赠白马王彪》诗意实自浑转。”(《唐诗三百首注疏》引)。喻守真曰:“读了自有一种至友挚情油然而生,亢爽天真,不作悲酸之语,可以想见其为人。” (《唐诗三百首祥析》)可见此诗不愧为送别诗中的极品。
杨炯所写的`诗现存者较少,但所写的离别诗却有几首,其《送临津房少府》是写得较好的:
歧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烟霞驻征盖,弦奏侯飞觞。
阶树含斜阳,池风泛早凉,赠言未终竟,涕泪忽粘裳。
而《途中》一首写游子的悲哀,直似汉魏风致: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涂路盈千里,山川巨百重。
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锋,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又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山川。预祝赵纵此去前途光明,写得豪迈动人。
卢照邻也写一些送别诗,较好的如:
津谷朝行远,冰川夕望曛,……谁怨仙舟上,携手独
思君。(《晚渡滹沱敬赠魏大》)
还有“寥落百年事,徘徊万里忧”的浩叹。
骆宾王写的送别诗比杨、卢为多。他的《送吴七游蜀》、《别李峤得胜字》都是很好的赠别诗,《于易水送人》慷慨激昂,笔力遒劲:
此地别燕舟,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诗题虽为送人,实则是借燕舟送别荆柯的故事,表达诗人悲壮激昂的感情。马茂云评曰:“把思古之情和别离之感结合起来,表现了极为激昂的现实意义,惜所送之人与本事已不可考。”(《唐诗选》)
总之,四杰将南朝着重于惜别情绪抒发的送别诗发展到可以熔铸社会人生实感的新阶级,为唐人“送行数百首,各以铿其工。”①的送别诗开拓了崭新的艺术道路。
四杰其他题材的诗歌也值得注意。怀古诗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闺怨诗摹写思妇情怀,细致入微,情致缠绵;咏物诗比兴寄托,暗寓身世……总之,绝少无病呻吟之作。
由此可见,四杰诗歌创作从根本上完成了初唐诗对象的转变和表现范围的扩大,使之“从宫廷走到了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示广阔的艺术天地:并由此改变了自六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诗歌路线,重新确立了诗歌反映显示和言志抒情的康庄大道。反映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抒发自己的人生情感是四杰诗歌的两大主题,后者更是经常咏叹的主旋律。他们诗中的浪漫理想和进取精神,仕途坎坷颠沛流离的人生命运,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勃郁之气,同样构成了当时文人的心灵历程。虽然他们的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不够广和深,还没有把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刻画出来,也比不上盛唐和中唐的某些优秀诗人,但是他们却代表了众多文人志士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文人志士的自我形象,正是诗歌的艺术准则。他们的歌唱,是唐代诗坛的第一个高峰,是南朝以来两百年间影响的第一阵春露,预示着诗歌繁荣时期的到来。其诗以表现社会化的人生情怀为主题,无疑已是盛唐之音的前奏。对于唐代诗歌的发展,其荜路蓝缕之功决不亚于陈子昂。
(二)诗体的推进
四杰诗歌创作在拓展题材和内容的同时,也大大推进了唐诗体式的完善。唐人将诗体作了鼎足而三的区分:“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者,名注体;其所变诗,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体,为近体;而七言古诗,于往体外另为一目,又或名为歌行。”
②值得注意的是唐人为何要将歌行单列到一目,从诗体的演进来看,五言古诗勃兴于东汉,建安正始间已取得辉煌成就,成为一种成熟的诗体。
无疑,五律也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七言诗虽相传在汉武帝君臣联句的“柏梁体”中孕育,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歌行则是曹丕《燕歌行》,其诗句之用韵,不失为言情佳作,但终有内容贫弱,风格柔靡之嫌。刘宋时鲍照、汤惠休等少数诗人有七言歌行的制作,直至梁陈,写作七言方蔚为风气。四杰对诗体的推进也就表现在律诗和歌行两方面。由于禀性不同,四杰在艺术上也各有擅胜。王、杨长于近体律诗,而卢、骆的歌行体更为出色,前者的近体诗显得紧凑,后者的歌行则气势充沛。当然,卢、骆也作五律,而王、杨中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并不在此。
从律诗形成历程来看,齐永明中沈约、谢眺等人创为“新体”,以声律的研究自别于古体诗。声律学说也在齐永明间产生,讲求音韵拘限声病的五言“新变体”由此产生。讲求声律的基础原则是从异声相配中突出声音高低起伏的节奏,以取得变化错综的音响美,即“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需切响”。因而注重一联诗内四声的相异安排,要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①至于两联之间在声韵上如何接合却没有明确的规则,通常是运用一种律联叠构成句,结果错误百出。为克服这一弊端,诗人们逐渐以两种律联结合使用,如将一种律联“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和另一律联“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结合,就形成: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的平仄格式。这就使两个律联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辅相成。在同和异的对立统一交织出优美的声律形式,取得良好的声律效果。由于上联对句和下联出句、上联出句和下联对句韵头相同,就形成了后世所谓的“粘”。《声律四谱》云:“单句成句,句不能成诗;双句为联,联则生对;双联为韵,韵则生粘。”齐梁以来的宫体诗也非常讲究声律的协调和婉,沈约等人提倡诗里调协四声,避免八病。他们虽片面追求形式而遭到过当时一些人的反对,但其中也有合乎语言声调自然发展规律的成分,为以后律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声律论的影响下,南朝诗人如沈约、何逊、徐陵、庾信等人,尽管他们仍以一种律联叠构成句为主,但参用两种律联的倾向已较明显,况且他们都尝试过律诗的创作,并在创作中不断推进律诗的发展沈德潜称赞他们已看唐人五言体。至唐初,时人特重偶时,但未能进一步发展沈、何、徐、庾诗中的粘联趋势。因而贞观以来到四杰前的代表诗人虞世南、唐太宗、上官仪等辈的诗,虽在用韵、属对上很见工夫,却往往失粘。相比较而言,沈、何、徐、庾的五律,,虽然格律不严,但已初具规模,有了协调和婉的特点,处于古诗到律诗的过渡状态。在他们的基础上,四杰进一步加以锤炼。四杰对五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前人诗作中的粘联趋势,使粘联构律成为一种主导方式,让同一律联叠构成律的方式渐淘汰。卢骆五言诗中古、律的区别已很分明,其律体大多合律,王杨律体几乎全部合律。例如王勃的《重别薛华》、《送杜少府任之蜀州》,杨炯的《有所思》,骆宾王的《秋月送别》、《在狱咏蝉》,卢照邻的《元日述怀》等,对仗工稳,音韵谐美,已是完整的五律,历来被人们所称引。四杰把正在发展中的律诗写得更加成熟,对于粘联的充分注意,使声律韵律、对仗为核心的格律规范趋向完善,从而完成了五言律诗的基本定型,这也为沈佺期、宋之问最后完成五、七律的格式奠定了基础。
在格律诗日趋精密的同时,是自由奔放、纵横驰骋的七言歌行大放色彩。律诗的创作,要求诗人在有限的篇幅和严密的格律中争取充分自由的艺术空间,使容量增加,意境深厚,才能显示出精炼而又丰富的美学性能。这对于唐代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对于才大雄厚宏放的诗人,不能不说是对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限制。
①所以唐人既需要格律诗,也需要能够施展其才力、驰骋其情志的歌行体。而唐代歌行体的充分奠定,正在于四杰继承梁陈诗人破奇为偶的句式,创造性地参用赋法,形成了偶对精切,音节可歌,“四语一转,蝉而下”,
②铺张扬厉,篇幅宏大的骈赋化歌行体制。
初唐时期,笼罩诗坛的是齐梁余风。那些宫廷诗人们,写了大量的侍宴应制、歌功颂德的诗篇,他们的七古,内容是粉黛佳人,歌舞***乐,情调缠绵,趣味不高,风格纤弱,不足为训,对七古的发展也没起到大的推动作用。四杰的出现给了当时的诗坛吹进了一些清新的空气,推动了七古创作向正确方向发展。在四杰手中,用七言歌行来写都市生活,诗的境界开阔了,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变动。四杰的七言歌行,一方面注意向民歌学习;一方面还注意吸收六朝歌行和小赋中铺陈排比、纵横多变的特点,扩大了诗的篇幅。他们的歌行虽未能摆脱六朝宫体绮丽的影响,却不乏通俗自然的诗句,也冲破了宫体诗的狭小内容,不同得反映了社会现实,题材比较广泛,风格已有明显的变化。在创制和发展七古上,四杰继往开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指出:“卢骆王杨,号称‘四杰 ’。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与微瑕,而缀绵贯珠,滔滔共远,故是千秋绝艺。”这段论述,对四杰的成就和不足做了正确的批评。
四杰中除杨炯未留传下七古外,其他三人皆有佳作。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尤为人们所重视。这篇七古,既有对上层社会生活的批判,同时又抒发了诗人旷达清高的情怀和愤懑不平之气,写得铺张富丽,气势雄放,一些诗句还比较通俗晓畅,轻快活泼,具有刚健清新的风格。可以看出,七古在他手中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同《长安古意》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都近似的,还有骆宾的《帝京篇》和王勃《临高台》。此外,骆宾王《从军行路难》中“征役无期返,他乡岁月晚”, “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等句,明白如话,表达了战士思归的感情。而“此时离别那堪道,此日空床对芳沼。芳沼走游比目色,幽径足生拔心草”(骆宾王《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月明露白澄清光,层城绮阁遥相望。遥相望,川无梁”(王勃《秋夜长》)之类的词句,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这种头尾蝉联的顶真辞格,又是学习六朝民歌《西洲曲》的作法,读来回环复沓,自然流转,特别是卢照邻《从军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写得十分豪壮,对高适、岑参的边塞诗,都有很大影响。卢、骆的七古,都有铺张闳丽,纵横雄放,以赋为诗,长篇巨制的特点。胡应麟《诗薮》说:“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正确指出了他们七古不足之处。的确,过分铺张藻饰,加上不太灵活的章法和句式,读起来象读汉代大赋似的给人以沉闷呆板的感觉,这也是诗家之大忌。
王勃的七古,只有七首,也存在胡应麟所批评的毛病,但在艺术成就上却高于卢骆。尤其是王勃的《采莲曲》,内容充实,风格清新,音调宛转,更是难得的七古佳作。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推崇王勃的文学主张和改革文风的功绩时,说他“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纷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翰苑豁如,辞林增峻。”这个评价,虽有夸大之嫌,但他倡风骨,并以创作实践力矫时弊,发展七古,取得了初唐时期张若虚之前的第一流成绩。以后,盛唐边塞诗派歌行、元白“长庆体”歌行,直至清代吴伟业“梅村体”,都是四杰歌行体的运用和发展。杜甫歌行以破偶为奇常用拗句见长,但其“《洗兵马》、《高都护》等篇,亦不废此一体。”
①可见四杰歌行为后来诗人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诗体范式,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四杰的七古,总的来说,气势雄放,铺张富丽;可是他们之间又不尽相同。四杰对诗体发展的贡献,也是与其重视音律分不开的。卢照邻认为诗歌创作应“含今古之制,扣宫徵之声”,“妙谐钟律,体会风骚,”感叹“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帝恐词林交丧。”
②王勃也说要“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节气”,
③以开创雄放刚健而音律协畅的文学。骆宾王在批评六朝诗“莫能正本”,并要求“弘兹雅奏,依彼***哇”时,也充分肯定了颜、谢以降“声律稍精”的艺术成就。
④可见四杰对音律的重视就是和题材内容的拓展、艺术境界的新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改变了齐梁诗人单纯在诗体形式上探索的风气,使诗体形式的完善充分地为诗歌内容的表现服务,大大开拓了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的艺术天地和发展前景。
(三)诗风的创新
艺术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艺术个性。“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
①这是长期以来对初唐文学承传新变的普遍看法。四杰诗创作也常被误为齐梁余风的继续。古人有所谓“不脱齐梁之体”,
② “犹沿六朝遗派”
③的指责。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贞观诗坛虽然有理论和创作的纠偏改良,但诗歌创作并没有发展根本性质上的改变,艺术上那种尚典丽、重骈偶、研声律的风习一直是主要的美学趋势。随着宫廷诗人对音律偶对的刻意讲求,“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
④的表现形式正适合宫廷风尚,加之,上官仪地位显赫,“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
④构成龙朔年间的一时风气。面对诗坛长期以来这种浮靡风尚,四杰深感不满,他们富于激情,锐意进取,追求昂扬阔大刚健有力的新的诗美理想。杨炯曾描述南朝绮靡轻艳诗风在唐的变本加厉的发展趋势,“尝以龙朔初载,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⑤ “上官体”过分讲求烦琐的雕饰,僵死的对仗,铺陈堆砌,以至于满纸金玉龙凤,朱紫青黄一派珠光宝气的色泽,四处句栉字节的浮词,缺乏昂扬劲健的艺术感发力,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用“绮错婉媚”的语言形式掩饰主体精神的卑弱空虚。在诗歌创作上,王勃声称大丈夫要“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时步。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情,日月自安于调下。”(《山亭思友人亭》),推行“气陵云汉,字挟风霜”(《平台密略赞·文艺》)的美学风格,以使廓清绮碎的文风,“反诸宏博”,(杨炯《王勃集序》)无创新的美学境界。卢照邻主张 “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受清虚,不以繁词为贵”(《驸马都尉乔君集序》)。骆宾王则更重视诗中情感的抒发:“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百忧交轸”(《伤祝阿王明府序》),认为“情蓄自衷,事符则感,形潜以内,迹应斯通”(《上吏部裴侍郎启》)。
四杰诗的风格也是变化多样的,有的朴素清新,有的沉雄壮阔,有的铺张扬厉,有的声色华美,各有各的风格,正如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所概括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藻厚,宾王坦易。”与齐梁以来的宫体诗相比较,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诗风开始转向刚健清新。一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宫体诗寄情声色的庸俗无聊的思想倾向。四杰诗也表现青年志士的英雄怀抱为主导内容,闪耀着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和乐观开朗的浪漫主义情调,有着生龙活虎的力量和欣欣向荣的情绪,即使抑郁愁苦,也是英雄受挫的悲鸣,而非庸人碌碌的颓丧,因而具有“刚健”、“雄壮”、“宏博”的特色,拉开了志在廓清“上官体”、“颂体诗”等浮华艳诗风,开创唐诗新境界的序幕和唐诗“风骨”美的先河。王勃自道:“若夫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春月孙学士宅宴序》)这种不平之气,不同与中唐以后孟郊之流的“感士不遇”,也不是叹老嗟卑,是刚健的,有冲击力的。诗歌被他们认为是抒发个人情怀最适宜的形式,向上进取精神及不平之气发之于诗,就形成了“浓郁的感情和壮大的气势”。
①这与绮艳夺目而淡薄寡情的宫廷诗相比,显得生气勃勃,使长期以来生气萎绝的诗歌恢复了活力,呈现出感人的力量和“生龙活虎般腾卓的节奏。”
②这鲜活蓬勃的生命力就是四杰提出得“风骨”的精神实质所在。他们又汲取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协和婉,从而形成了雄放刚健、柔润美丽两相兼济的总体艺术风格。如果说齐梁诗风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下掩盖着江南弱女贫血的面庞,呈现出一种病态美,那么四杰诗风则如燕赵十八女儿,虽丰姿美艳,却秀色天成,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矫健可爱。
③前人谓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
④借来比喻四杰诗风最为恰当。许学夷云:“四子才力概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诗源辨体》卷十二)四杰的意义就在于开盛唐诗的道路。此后盛唐时期之李、杜、高、岑等人,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也无论其是否进士出身,最初都是以下层士子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壮大劲健诗美的追求,与四杰是一脉相承的,往往呈现为刚健之力和飞动之势。
无可否认,四杰诗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南朝诗歌的流风余韵。譬如讲求骈偶,铺陈辞藻,时有堆垛之嫌,略露板滞之弊,谭元春批评骆宾王诗有时“极滞极拙”,正是这个道理。
①有些字句雕琢过分,以至于语义难解,如王勃诗“流水抽奇弄,崩云洒芳牒”,“帝里寒光尽,神皋春望浃”,
②就是如此。但是瑕不掩瑜,他们诗歌语言的主导倾向,却是发展了六朝诗歌绮丽而清新、藻绘而自然的长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了浏亮精工、美丽和婉的语言风格,这是在承继中新变和创造。在这总体语言风格统摄下,所以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语言又各具特色。五言趋向于偶对精切,疏朗工稳,时有刚健之气;七言则骈偶藻绘,秾艳动荡,流利畅达,和婉可歌。由于四杰遭受挫折后,缺乏拼搏到底的精神,不如盛唐诗人那样经受着生活得磨难而仍不失昂扬进取得胸襟和乐观开朗的情怀,诗境未免局促,清新有余,深厚不足,缺乏渊灏之气;又以文采与时争胜,对六朝诗弊病认识不足;语言上新创不够,未能将华茂词采提炼到纯熟自然,妙造天成的艺术境界。这是历史的局限,但这并不能抹杀四杰诗歌的光辉,此后陈子昂的成绩正是在四杰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形成,把四杰创建唐诗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综上所述:初唐四杰实为初唐九十年诗歌发展历程中关键性的诗人,不仅是六朝诗的变革者,更是唐风初见的先行者。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诗体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创唐诗独特美学风格的风貌,不仅给沈、宋,而且更给陈子昂、李、杜、元、白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把唐诗发展到完全新的阶段。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特点,但一方面这也是由于骈偶文丽文的影响以及个人对于文采的美的追求,这与齐梁陈的浮艳之风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总之,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即越过齐梁直接晋宋,下开盛唐)的作用。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同照邻可以企之。”李白说:“骆宾王为诗,格高指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诗人玉屑》卷十二《李太白集》),可见四杰的诗文很受唐人的重视。杜甫也在其《戏为六绝句》中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见,唐人对四杰作了很中肯的评价。这就是“四杰”,历史的“四杰”扬之不可高,抑之不可太低。时至今日,无论是毁是誉,他们作为唐诗的第一座丰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拓展
初唐四杰是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为“王杨卢骆”。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转载请注明出处记得学习 » 初唐四杰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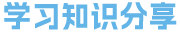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