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名词解释
导语: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也是文人追求的风格特征。下面是语文迷收集整理的关于魏晋风流的介绍,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魏晋风度如此光彩夺目,无非是因同其他时代相比,这些人显得不太一样。说是不同,简单说就是价值逆反。而从今天来看,这种看上去更自我的形象,无疑显得有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魏晋风度基于人的觉醒。荣华富贵朝存夕逝,学问信仰昨是今非,人生无常与性命短促挑战着宿命论的权威。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指引着魏晋名士们进行着向内的自我探寻。短暂的生命,死是必然。这种悲伤颓废的人生观的背后则是魏晋名士对人生与生命的无限眷恋与强烈欲望。然而没有什么是可靠的、真实的,除了即时的欢愉,这便是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种价值观看似贪*享乐,堕落消极,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生活的率真、坦诚却又无力的追求。想要把握住这种充满苦难而又短促的人生是一种虚妄,“不如饮美酒,批服纨与素”,把生命、人生寄托于一种更为虚妄的虚妄之中。
说到魏晋风度不得不再闲扯点吃药的事,为了使皮肤变的弹指可破,他们吃很多奇怪丹药皮肤溃烂红肿所以穿袍子,袍子经常不洗,生出很多虱子,所以又有扪虱清谈一说,穿袍子或许更是是为了抓起来方便,吃药的祖师爷是何晏,当时他吃的是一种很厉害的“五石散”,大概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这几种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有毒的。这药贵呀,何晏有钱任性,吃完药通过疾走“散发”,便可免于毒死。疾走时吃药的人先是全身发热,后又变冷,此时需要吃冷东西,少穿衣服,冷水浇身。全身发热又让他们皮肤灼烧而必须穿宽袍,所以看见穿宽袍疾走的魏晋名士,觉得他们风度翩翩,实际上是吃药作的.……后来东晋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假装“散发”而摆阔,让我不禁为现代人辛酸,这充胖子的成本连打肿脸都不用,实在是太低了!这部分的内容,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有详细记载。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大多死很早,穷而狂傲,逃避现实,话说当时刘伶在他的木屋里也就是他家是红果果的状态,还与猪同饮。某日一人闯入他家见到他的玉体抱怨他不穿衣服,他对某人如是说:我在我家里不穿衣服是因为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闯进来就像突然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到底是谁更应该羞愧。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
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孟德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流职场启示
故事:
关心时尚的请免进,因为我讲的不是鞋,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中国历史上有个时代,名为魏晋时代,这个时代总被打上“风流”的标签。是怎样的一种风流呢?先讲一个故事。东晋时有两个收藏癖。一个叫祖约,大家或许不知道此公为何方神圣,但总知道“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祖逖吧,祖约就是这位北伐志士的嫡亲弟弟。祖约喜欢收藏钱币之类的玩意,乐此不疲。另一个叫阮孚,阮孚喜欢收藏木屐,也为之废寝忘食。
两人都是收藏发烧友,谁的境界高呢?某日,某人不请自来到了祖约府上,祖约正在料理财物,忽见人来,慌忙用身体遮挡那些收藏钱币的筐子,言谈举止大失常态。
某日,某人忽然造访阮孚府上,却见阮孚正在自己吹火给木屐上蜡,一面做,一面叹息:“哎,此生不知道能穿几双鞋呢?”神色如同在闲聊一般舒畅优雅。
故事结论:
《世说新语》记载下了这则轶事,并给出结论:于是胜负始分。
按魏晋时的评判标准,阮孚胜,祖约负。这个胜负是指人生态度的一种胜负。不看谁迷得深,而是看谁把持得淡定。祖约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在钱币上面,被这些“身外之物”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人生当然“负”;阮孚虽着迷木屐,却跳得出来,保持得淡定,不为自己的爱好所奴役,这样的人生,当然“胜”。
魏晋时代评判人物不只看成败,更要看能不能从成败中跳出来。事业可以输,风度不能输。套用一句话就是:哥比的不是事业,比的是境界;哥比的不是成败,比的是风度。
人的一生,总是在一个有限的框框里发展。你的使命,就是把这个框框里的内容做好做精彩。然而,我们在把框框里的内容做好的同时,不妨也要跳出框框来看一看,如此才不至于被这个框框所累。做好框框里的内容,那叫敬业;跳出框框来看,才可以淡定。所以《三国演义》在开卷之前,先给读者一杯消火的凉茶: “是非成败转头空。”就是提醒了要你跳开来看三国的成败。
东晋人物谢安,淝水之战的军事总指挥,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他没有发牢骚说:你有压力,我有压力。而是以跳出大战这个框框的态度指挥大战。他在后方指挥所下棋,前方捷报传来,他将自己一生最漂亮的成绩表藏在袖子里,继续下棋,有人问起,轻描淡写一句:儿辈在前线大破敌军。
古人如此,今人该如何?我们还需要像阮孚那样一面做业务,一面感叹一生能做几张业务单吗?
我的看法是:需要,比古人更需要。因为在商品社会,财富容易泡沫化,成功也容易泡沫化。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胃口和偏好上。消费者的胃口和偏好造就一个短时期的繁荣,养活一大堆经理、董事、骨干、白领。这种奇迹有如狂风暴雨般骤然而来,但也如老子所曰: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过几年,市场的需求和胃口变了,你还来不及高兴,业务单、成绩表就落花流水春去也,新的业务又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所以,在热闹中不妨有一种冷眼光,在喧嚣中不妨有一份静心思。竞争时代,胜与负没有中间地段,业务拿不下,你就无地自容,非胜即败,心灵很容易在胜与败两个极端境地的高抛高落中粉碎。所以,要给自己营造一个缓冲地段:淡定。
打出业务上的淝水之战
如果跳不出来,局限在成败得失的计较中,这种态度就决定你的人生失败一半了。东晋将军殷浩因为战败被罢官在家赋闲,他对自己丢官一直耿耿于怀。权臣桓温想重新起用他,殷浩马上给桓温回信,可这位仁兄太不淡定,生怕写错,于是屡次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改写,以至于最后将一张空白信纸装入信封,桓温大怒,复官无望。殷浩难以释怀,一天到晚用手在空中写字:咄咄怪事。最后郁郁以终。
民间说老不看《三国》。年纪一大把了,也该跳开来看自己的人生,站在一个高度审视成败了,却还陷在历史演义的成败纠葛中不能自拔,何必?何苦?
只有跳出此山才能看清此山,只有跳出棋局,才能看清棋局。所谓旁观者清,你也要试着做你自己框框的旁观者。你淡定了,在你的职场,你就是谢安,你就能打出你业务上的淝水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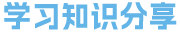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