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蒲散文
蒲,一般生长在村野的河滨或者沼泽之地。蒲在城中少见,或许在某些公园里能够看到,但少有人问津。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他的茎叶很长,修长的叶子呈现诱人的青绿色,高达三到四米,纤维柔韧,可以编席、织扇、做垫。
突然提起蒲的话题,是因为我今天去了一趟乡下,在一个村子的入口处,一座汉白玉石的小桥静卧在一条清幽的河水上,一踏上那条蜿蜒在村庄面前河岸,氤氲的凉气直逼胸前。时值盛夏的七月,流火的季节,高达37度的气温,竟然有如此凉爽的地方,不免要寻找一下原因。
除了河的两岸长满密密麻麻的的蒲外,就是一河碧水在流淌,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观。行走在岸边,那高高的蒲形成了高过人头的绿色围墙,它的绿荫遮挡着一半的路面,微风吹过,不仅掀起了绿色的起伏的波浪,也将蒲那特有的清香赶上了岸上,直逼行人的丹田。细看,密密的蒲叶中间间或地点缀着一些蒲棒,似一根根棕色的蜡烛点燃其中。
又见儿时的乡村景,心海中迅速涌来童年时光的关于蒲的那束浪花。
掀起时光隧道的门帘,走进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个码头。一天滚滚东去的排洪大河波涛汹涌,飞溅起洁白的浪花,沙鸥追逐着东来西往的白帆,洁白的鹭鸟也时而翩飞时而俯冲水面,河岸生长着高高的蒲,由于河岸很高,那些蒲只能够露出梢头,仰望着岸边的村庄既岸上的行人,微风吹拂,远望似拂动的青绿色的缎面,而近看又若在与河水共舞。
那个年代,蒲在农村的作用很多,与农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到夏季,人们就会拿起玄月般的镰刀,去收割一些蒲,晒干后,人们寻找空闲的时间,去编织一些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阴天下雨的时候,时间比较宽裕,人们往往拿过那些干蒲,麻绳为经,蒲叶作纬,手脚麻溜地编织起蒲席来。别看这种用半原始的手工技术编织成为的蒲席,外观粗糙,其貌不扬,但却拥有当今那些高档席子无法具备的特性——冬暖夏凉。夏天铺在床上,吸汗透气,清香扑鼻,与生俱来的凉气,即使天气首发炎热,也保证你的身上不会长出痱子。倘若你冬天将它铺在床上,由于它纤维细长而柔软,受热膨胀,又具有很强的保温性。同时,它的可塑性大,可叠可卷,携带方便,所以蒲席在那个年代深受人们的喜爱。
蒲团,在当今的社会中,可能在一些禅寺中可能还看到,那是供僧人打坐、念经时使用的,一边微闭双目,敲着木鱼,一边念念有词,心入禅境。更多的是供香客烧香跪拜敬佛时使用,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蒲团,使得敬香的人不至于双膝酸痛。不过,这些蒲团大多被覆以绫锦,看不到蒲团的外表,只能够让你感到舒服。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心灵手巧的妇女们在有空闲时,除了编织蒲席外,更多的时候会用蒲草去编织蒲团。编织蒲团除了要有一定的经验外,还要有一定手劲及其耐心。我曾经看过妈妈编织蒲团,开始要编织一个马莲座,然后再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编织到大约三十到四十公分直径的圆时,再收口编织圆柱体,然后再收口向里编织,最后,就成为了高约五六公分的圆柱形坐具。当然蒲团有大有小,分为成人和儿童使用二种。
蒲团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使得坐上的人感到舒服。特别是那些小儿,容易尿湿,但不要紧,不会大面积地尿湿衣服。由于它轻便,容易携带,使用好多农人串门、去听书,或者去看社戏,往往使用它去做坐具。同时,即使丢失了,也不至于过分地痛惜,大不了明年夏天在去河边多收割一些蒲而已。唐代诗人欧阳詹曾经做了一首《永安寺照上人房》的诗:“草席蒲团不扫尘,松间石上似无人。”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了端坐蒲团那怡然自得的心情和感觉。
七十年代的夏天,农村人纳凉坐着的是蒲团,躺着的是蒲团,手里总少不了拿着一把蒲扇,不仅可以驱赶昆虫和苍蝇,更重要的是祛暑扇风,摇来自然清香的清凉,带走暑气和烦躁。尽管文雅的人会轻摇羽扇,识字的人慢扇折扇,姑娘们拿着形状不一的绣花绸扇,小伙子则使劲地时尚的芭蕉扇,但更多的人是在使用麦秸扇和蒲扇,特别是那蒲扇更为普遍,它不仅带着千古的风韵,也带给人们怡情和自然的风,同时,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假如你偶然遇到三、二人汇聚一起,放下扇子就可以席地而坐,不仅不会让衣裤脏了,起来后轻弹几下,则又干干净净,恢复原状。
在夏季的月色下也好,黑纱中也罢,纳凉的人们最喜欢使用蒲扇,那是因为蒲扇的气息天生就有着驱赶蚊子的作用,数把蒲扇同时摇动,那蚊子就会躲得远远的,在夜晚,人们还会点燃一些晒干的蒲棒,一明一暗地燃烧着,升起袅袅升腾的烟雾,其芳芳的气息极具驱蚊作用。燃着的蒲棒一般会插在地面上,但有儿童的时候,它不是变成左右晃动的红色光线,就会在半空中划着圆弧……
蒲,虽然有驱除昆虫的作用,但有一种昆虫却会如胶似漆地黏上蒲,那就是好多人都喜爱的蜻蜓。无论你在盛夏的什么时候,走近长满蒲的河滨,你都会发现那修长的蒲叶上总会栖息着一些五颜六色的蜻蜓。鲜红的、鹅黄的、翠绿的'蜻蜓,一个个平展着透明的翼翅,震颤着,恰似一架架袖珍的飞机,时刻准备着起飞,蒲如同荷一样,对蜻蜓有着无穷的魅力和诱惑。
蒲的常见用法还有好多,比如他的纤维很长,便于搓绳,由来捆扎什物。又因为它耐水浸雨湿,沿海的地方往往用它去编织成为蒲包,去装盛运往外埠的盐,或者直接去覆盖盐堆或者在雨季铺在盐池边道路上。在春夏之际,细心的人还用它去编织成为蒲鞋,既经济实惠,又舒畅而凉爽。而到了冬季,人们又利用它的保暖性,又将它和芦苇上的荻花一起去编织成为草蒲鞋,看是其貌不扬的鞋子,可穿起来却十分暖和,恐怕少有棉鞋可以和它相匹敌。
蒲,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好多用途,在初春,它的嫩叶及茎根都是可以用来食用的,是一道地地道道的淮扬菜——蒲菜,还拥有一个与历史有关的菜名——抗金菜。
传说,在南宋有一位近乎与岳飞齐名的主战派——梁红玉,为了保卫南宋的江山,誓死保卫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在淮阴(今天的淮安市)与金兵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峙,可昏聩的南宋朝廷连军粮都难以接济。就在梁红玉忧心忡忡去巡视兵营时,被她发现马食用蒲茎的现象,她随即从战马上跳将下来,走到长满茂密蒲的水滨,用战剑削下一根蒲茎,放在做里一嚼,不仅吃嫩,而且十分爽口,从而解决了她一直担心的军粮的维系问题,并大胜了金兵。
后来,蒲茎可以食用的消息传到民间后,经过厨师的不断翻新研制,使得蒲菜在当地的宴席上成为了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并成为了宴席上的上品。“开洋扒蒲菜”就是其中之一的名茶,它运用春末夏初的嫩蒲茎,配以虾米、鸡汤,吃起来:细嫩爽口,汤汁清鲜,清香似溢。到今天还是两淮地域的时令佳肴。
因此,蒲茎,虽然出自污泥,却洁白赛玉,宛如葱梗,鲜嫩清香,特别在入冬之时,人们不惜高价购买的现象,已有多年。
或许你会大惊小怪,但,蒲菜入席,并不是梁红玉的首创,早在二千多年前,蒲菜已经捷足先登在大雅之堂。在《周礼》上就有关于蒲菜的记载,明朝的顾过曾经说:“一箸脆思蒲菜嫩,满盘鲜忆鳗鱼香。”
在中国,蒲文化早已根深蒂固,并浸染到九五之尊的封建皇帝,曾经的皇上,都有登泰山封禅的习俗,每每去泰山,常常是用蒲将乘坐的车轮子包裹起来,是迷信也好,减震也罢,但,却有一番亲和力,显示着他们爱惜民生、感激草木之情。
在中国的古代官场上,都有一把轻柔似棉、打人不疼的鞭子,原来鞭惩懈怠之人,喂之仁政,这边如同上方宝剑一样的鞭子,就是用蒲做成的。唐诗人吕温曾经对挚友说过:明朝别后无他嘱,虽是蒲鞭也莫施。其意是说,治理一个地方,蒲鞭高挂不用,才是出色的治理之道。
蒲,确实有着天生的亲和力。记得小时候的我,在柳绿花红的初春时节,常常会去摘下一片刚刚发芽生长的蒲叶,将它从梢头一直卷到尾,形成了一个圆形,层层叠叠的叶缘就形成了无数个同心的圆,再摘取二根刺槐的针子扎在尾部,固定一下,让它不至于散开。看起来就像当时使用的闹钟一般的外形,只要将它迎着阳光看,它就会产生二根如同时针一般的光影,当然那纯粹是为了玩而已。
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采摘蒲棒的机会的,孩童倒不全是为了用它去驱除蚊虫的,主要是为了蒲棒在晒干后,轻轻地划破头部,然后用嘴轻轻一吹,就会絮舞雪飞般地飞扬起来,如同吹散蒲公英的花絮一般,充满神奇的想象的空间。
收割留着使用的蒲,往往是大人们的事,哪一个家长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经常到大河边去玩耍,水火无情,自古亦然。即使到了秋霜飞舞,摧枯拉朽之后,收割枯萎的蒲草回家当着柴火烧的事,也是大人们的事。
纵观蒲的一生,它具有着莲荷一般的品质:出污泥而不染,奉献给人们好多用处,但它常常独处河滨一隅,有时还钻到芦苇荡的隙缝中生长,有着不择水土的习性,从不追求人们的眷顾,独自生长。尽管如此,人们对蒲却极度不公,在关于蒲的相关词语中,不是与谦卑相连,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就是与贫贱在一体,比如《战国策》中说伍子胥:“尘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就是到了现在,蒲,甚至与“鬼混”相关,如“夜蒲”一词,就是指夜生活,有疯狂地玩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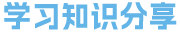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