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冰雪美人》赏析
《冰雪美人》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悲剧女子.其主题有多重,既批判“白马镇文化”,也批判丑陋的人性;既反思现代价值观,也反思社会转型期人的思想现代化的重要性。下面是整理的莫言《冰雪美人》赏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内容简介:
《冰雪美人》是莫言作于2000年的一部短篇小说,它通过描写主人公孟喜喜因为长得太漂亮,加上她那独特的傲立于冰雪的性格而引起我们这个社会群体的嫉妒和排挤,最终被人们用冷漠和鄙视无情地“杀害”了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传统观念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作品写了一个颇似“红颜薄命”的凄美感伤的故事,也是一出关于美的毁灭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主人公孟喜喜本是一名女学生,只因为长相出众,又懂得打扮,加上个性活泼开朗、不苟言笑,因而在那所“十分保守”的乡镇中学里总显得“太过分”先是被年级主任视为异端,大加挞伐,后被学校以“作风不正”宣布开除。回家后孤女寡母合力经营鱼头火锅餐馆,却又因她“化着浓妆,站在店门口招徕顾客而招致种种非议,声名狼藉。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里,她来到镇上惟一的私家诊所就诊,不料医生忙于给两个后来的急诊患者施治,受到冷落的她竟寂然倒毙。
赏析:
读罢莫言的短篇新作《冰雪美人》,掩卷沉思之间,女主人公孟喜喜临死前那“冰一样透明”的脸庞渐渐凸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是那样的令人心生寒意而又让人肃然起敬!如果说石舒清在《清水里的刀子》中是把宗教情怀赋予那被杀后“硕大的牛头”,使人们感动于那张“颜面如生的死者的脸”;那么,莫言则是满怀着对生命的敬意、对自由和美的崇拜,让我们震撼于那张冰清玉洁、将死而又不改其从容不失其尊严的生者的脸。我相信,每一位敬畏生命的读者都会和我一样对孟喜喜的意外死亡悄然动容,甚至潸然泣泪;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倘使人物命运失去了其艺术真实性,则无论接受者有多么强烈的情感反应都是肤浅而不可靠的。
因此,我们在感动之余完全有必要对小说文本质疑问难:孟喜喜的非自然死亡有没有其必然性?谁该为她的死负责任?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探询和解答不仅关系到我们对小说人物形象的价值评判,也关系到对作家艺术匠心的理解与把握。
我们从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得知:孟喜喜的直接死因是延误了诊治。那么,作家在小说中设置的“延宕”有无必然性呢?我们自然不能忽略小说中两个极其重要的情节:一是孙七姑之母的化脓性阑尾炎急需手术;二是被连珠炮炸暴了眼珠的马奎需及时处理。这两个情节虽然也还衔接得不算牵强,但显然带有太多的巧合。这种巧合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作者在情节设置上似乎过分追求戏剧性而有失其必然性。然而,小说文本的自足和复杂却告诫我绝不能如此草率地作出定论。
这里,我们有必要细味一下小说对管医生在孟喜喜急切求医之时反而动作迟缓的描写:初到诊所,打完身上的雪,“又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抽起来”;拿茶叶时甚至还在手心“掂量了一下”;第一个手术前先“咕咕嘟嘟地灌下半缸子水”;手术完了“坐在椅子上吸足了烟喝饱了水”才开始理会孟喜喜,但立即又被新来的病人打断了。叔叔“特别能喝水”的生活习性在这里成了他延缓时间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家为什么在小说前半部分要用整整一大段文字来浓墨重彩地渲染叔叔嗜茶如命的怪癖。其实,叔叔对医生这个职业并无多大热情,而且“又是一个骄傲透顶的家伙”,这样的医生自然不会对病人有好脸色。更何况,叔叔对孟喜喜确实存在着偏见。
当“我”告知他病人是孟喜喜时,他“哼了一声”说:“她能有什么病?”当孟喜喜招呼他时,他又是“哼了一声,根本不看她”,他对病人的冷漠与傲慢在此表露无遗。危急之中的孟喜喜求救于这样的医生,又遇上那么巧的“干扰性”事件,自然就在劫难逃了。
至此,我们可以较确凿地说:莫言所设置的“延宕”意在彰显医生的傲慢和偏见,而正是这种傲慢和偏见导致了孟喜喜难以避免的死亡。然而,作者却不仅没有把管医生写成一个大恶之人而成为孟喜喜的对立面,而且对其愤世嫉俗的性格还颇有些欣赏之意。这是否与作者同情孟喜喜的情感指向有矛盾呢?我认为,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处理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显示了莫言的匠心别具:《冰雪美人》再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医德或抨击世风的作品。作家清醒地意识到许多类似管医生的愤世嫉俗者固然也是出自向善的心理动机而对孟喜喜这样的所谓“堕落者”深恶痛绝,但是又有几人真正关心过他们的现实处境、探究过他们“堕落”的深层原因呢?
如果只是作出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姿态,那也许很容易,但是往往很难有感同身受的理解。正因为就连管医生这样对世俗社会有一定程度超越精神的人都轻视孟喜喜,我们才更深刻地理解孟喜喜在社会中找到精神上的认同者是何等艰难(“我”父亲为孟氏母女的辩护只是一种同情而不是精神上的价值认同)。
因此,管医生作为非反面形象(当然亦非正面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致命的偏见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让读者心头的寒意更为浓厚,从而引起我们更多更深沉的思索。
诚然,叔叔对孟喜喜的偏见也不是没有缘由,就连一直暗恋孟喜喜的“我”都相信她“干上那行了”,对她不甚了解的“叔叔”就更加会把她视为低俗之人了。但叔叔的态度又与年级主任对孟喜喜的歧视有着极大的不同。年级主任对孟喜喜的恶毒攻击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校纪校规,而从其潜意识来看就是出于一种嫉妒——对孟喜喜的美貌和青春的嫉妒,人性之恶在年级主任对一个清纯少女的精神迫害过程中得以彰显,令人不寒而栗;而那些对孟氏母女说三道四的人也多半是出于与此相似的又一种嫉妒心理——对别人拥有财富的嫉妒。
虽然叔叔开初是把孟喜喜视为众多风尘女子中的一员而冷漠相待,但我认为叔叔最终还是意识到了孟喜喜超俗的个性及其独特的精神价值。这可以从叔叔最后全力抢救孟喜喜的焦急、抢救失败后的沮丧以及呵斥婶婶的愤怒等表现中得到充分的印证。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医生抢救病人的正常反应,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认为,对于一般的医生而言,也许的确如此。但我们绝不能忽视管医生作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更不能忽视作者在小说开头不惜以较多篇幅凸显管医生鲜明个性的用心所在。他的`行医哲学是“当医生其实和当土匪一样”,“真正的大医生看起来像杀猪的”,他在手术台上搞实验,“把几个不该死的人给治死了”。
像这样一个一贯“胆大包天”的医生何以对孟喜喜的突发性死亡独能有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呢?比较合理的解释即是:他以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与孟喜喜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契合,孟喜喜的现场表现又使得他将这种潜在的契合感受挑到了意识的层面,于是,他对自己先前的傲慢和偏见已有了深深的内疚,孟喜喜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使他受到了震撼;而且这种内疚的强烈程度与孟喜喜精神的高贵显现是相伴而生的。我认为,孟喜喜临死前的精神魅力就在于:承受巨大痛苦的坚强以及在生命尽头所展现的优雅与尊严——这无疑是“冰雪美人”这个形象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孟喜喜与莫言早期作品中一些人物形象在精神特质上的一脉相承。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都是亲属,好像一父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有显著的相像之处。”我们不妨再具体一点说:作家在不同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亲属,彼此有显著的相像之处。
比如,我们完全能够将孟喜喜视为《红高粱》中罗汉大爷、甚至曾经作恶的余大牙的后裔。罗汉大爷在被剥皮时的那种神一样的尊严给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就是那个因***民女被*杀的余大牙在临死前也表现出了令人难忘的“英雄气概”。莫言曾在《红高粱》中写到:“人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都会使人肃然起敬。”孟喜喜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不仅仅是在那令人感叹的一瞬,而且也更多地体现在她最后几个小时内与死神顽强对抗的全过程。她始终都是那么优雅从容,那么彬彬有礼:进屋前是传来“轻轻的敲门声”,然后是“客气地对着我点点头,柔声问我”,听到回答后又“微微一笑”,当叔叔进屋后,她是“站起来”打招呼……与周围那些猥琐之人相比,她简直称得上高贵了。最让人震动的是当她病情不断加剧而叔叔又无暇顾及她时,她所表现出的那种隐忍和坚强。
当叔叔第一次撇开她时,“孟喜喜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在这“想说”和“没说”之间潜伏着何等激烈的内心冲突和肉体痛苦!当孙氏兄弟在屋内制造出浑浊的空气时,“孟喜喜脸上的汗珠子成串滚下,表情十分痛苦,但她的身体还保持正直……”;“我”叫她喝水时,她“痛苦的脸上挤出一个扭曲的微笑”,还低声道谢;“当我满怀着同情和歉疚看她时,她对着我摇摇头,似乎在劝解我,或者是在告诉我她对叔叔的行为表示充分的理解,而她自己并不要紧”……在这些令人心颤的细节中,孟喜喜虽然经历着生与死的痛苦挣扎,但她始终都没有像另外两位病人那样大喊大叫。那两位是故意夸大自己的病痛,表现得尤其懦弱,而孟喜喜恰恰是竭力压制自己的痛苦,尽量保持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
孟喜喜的肉体生命或许是脆弱的,但她精神上的勇毅与坚韧却会令许多号称“强大”者汗颜。和罗汉大爷等人有尊严地面对死亡相类似,孟喜喜之死的人性启示意义即在于:尽管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各种痛苦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却可以凭着强大的意志力量使自己在面对痛苦和死亡时获得人类理应持有的尊严,从而在精神上对痛苦和死亡作出可贵的超越和升华。
我们自然无须把孟喜喜的隐忍生硬地提升为先人后己的高贵品质。如果注意到她在学校时承受辱骂和责罚的那份坦然与平静,我们就会发现:孟喜喜这种强忍痛苦而保持从容的生命姿态正是她一贯受辱不惊的精神气度的显现和延伸。因此,孟喜喜对管医生的怠慢并不是太在意,与在学校里她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相比,管医生已经算够客气的了。换言之,对于受惯了年级主任之流的恶毒攻击和世人冷眼的孟喜喜而言,叔叔那含义模糊的“点点头”也许已是对她极大的尊重了。
由此,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年级主任对孟喜喜的心灵戕害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她那有失教师身份的恶毒让年少的孟喜喜过早地体验到了人心之阴冷、人世之险恶;使她逐渐地习惯了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正,从而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姿态,并用这“不在乎”维持着自己有限的自尊。同时我们也才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孟喜喜平常生活在一个怎样严酷的环境中,又忍受了多少屈辱与伤害。因为,当一个本性善良的人长期承受太多会压力所致的痛苦时,他就会因承受力的加强而忽略或轻视很多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痛苦。
如果说孟喜喜隐忍的性格是导致她死亡的内因之一的话,那么我们绝不能说她是自作自受,因为形成这种性格的基础除了她的本性善良之外,还有环境的因素。
孟喜喜的意外死亡虽然只是发生在诊所里,但是却与年级主任以及那些冷酷的社会心理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牵连,孟喜喜的悲剧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所致,而绝不仅仅与管医生一人有关。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算对本文开头的问题有了较明确的回答,至此,我们也才较准确地触摸到了这个悲剧故事的内核。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我认为孟喜喜作为受难者形象的价值就显现于她被毁灭的过程中。当听到她最后那一声“悠长的叹息”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如此感叹:她死得多么像一位圣徒啊!“冰雪美人”的意象在此刻获得了圣光照耀而动人心魄。
对于充满同情心的读者来说,谁都不希望孟喜喜就此死掉,但就艺术形象的圆满性而言,正是她意外的死亡成全了“冰雪美人”这一雕塑般的形象——莫言正是以合乎逻辑的人物命运轨迹实现了艺术的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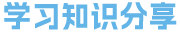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