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退之由来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下面是整理的韩愈退之由来,一起来看看吧。
退之由来
韩愈,唐代诗人,文学家、散文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愈名字的传说 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
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 翻开书年,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
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嫂嫂为他起名作难,便问:“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人去群之首,会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字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
”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
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 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了,他却名落孙山。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又一连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完婚。卢小姐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
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暗道:卢小姐果有见她,接着说道:“小姐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请小姐赐教。”卢小姐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 “ 人求言实,火求心虚,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总结:韩愈捧赠言,一阵沉思:此乃小姐肮腑之语啊!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这个“愈”字便是证据。于是,他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给自已起了人个新名字。
主要影响
文学
韩文
主词条: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怒涛”、“***”以及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教育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后又任国子监祭酒。他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5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3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
《顺宗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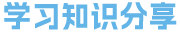 记得学习
记得学习